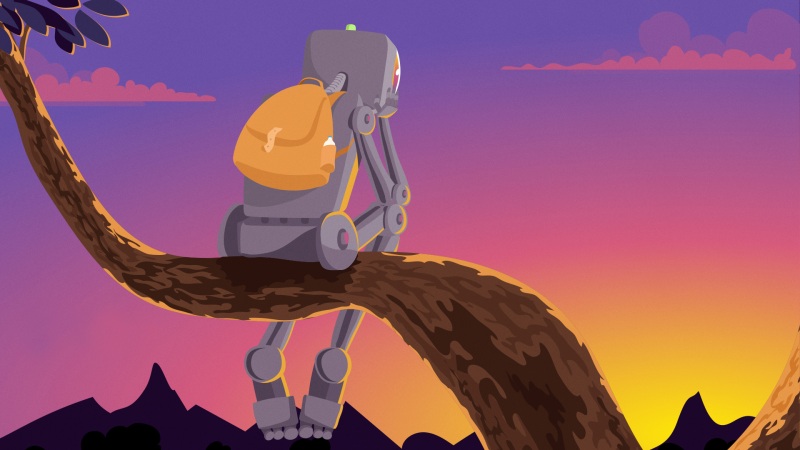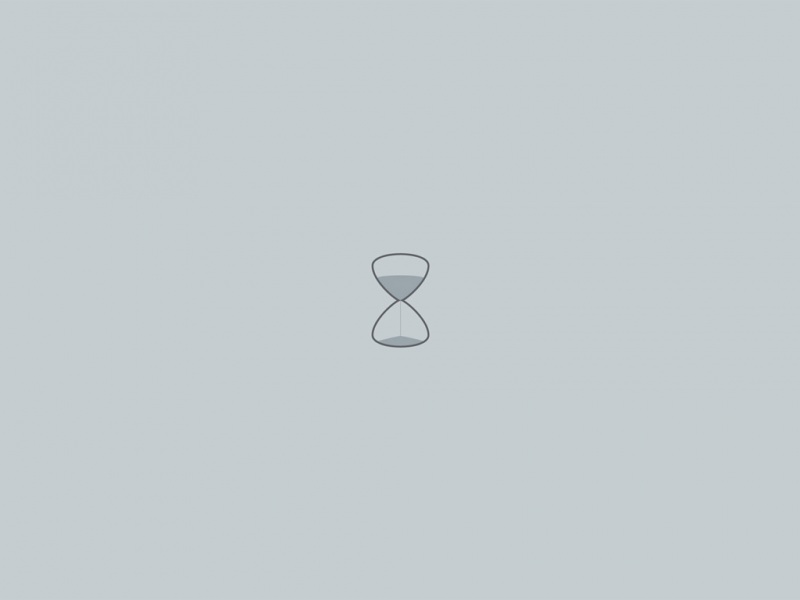在朱天文眼里,侯孝贤拍《刺客聂隐娘》,就像是跳起前的那个蹲下。既是用武侠,这种看起来和侯孝贤电影最不搭界的类型,对自己成熟度来一次考核,也好比要想再一跃而起,往往要先俯身蹲下,一个盘整的姿态。“68岁来拍《刺客聂隐娘》,像是把过往的那些很强的电影功力累积沉下去,蹲下去,未来的一个吧,他说希望能每两年拍一部,再能够拍个10部,就已经88岁了。可能前提就是这样的一个盘整,《刺客聂隐娘》里他所做的事情。”
找寻唐风古韵
不过回溯记忆深处,朱天文说,听侯孝贤讲聂隐娘的故事,竟也足有30年了。可是那时候朱天文觉得,那不过是一个很遥远、说说而已的迷梦。
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是唐代传奇的重要文学渊源,它在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巫术、方术和其他宗教迷信的影响,而唐代盛行的游侠思想又更加使得带有宗教色彩的豪侠小说在晚唐成为一大文学风景。《聂隐娘》(《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四录)正是此类传奇的代表作之一。这个题材和侯孝贤电影是疏远的。聂隐娘静心苦练打熬练成剑术,似乎也会了隐形术,“人莫能见”,又似乎自然而然地通达了变形术,甚至在她得知妙手空空儿前来偷袭时,已了解到其神术“能从空虚而入冥,善无形而灭影”,化为蠛蠓(小飞虫)进入到人的肠中躲避,分明就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前驱。这跟开拓台湾新现实主义的侯孝贤电影,更是南辕北辙。
朱天文也没想到早在2000年,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似乎就有了眉目。那时从《好男好女》(1995)一路与侯孝贤合作的电影美术指导黄文英,就真的把它做成了一个企划案放在了网上。于黄文英而言,对《刺客聂隐娘》的热情是从《海上花》一路走来,顺理成章。1998年《海上花》给黄文英夺下了金马奖最佳美术指导奖,她自己也觉得这是具有某种小结意义的作品。“侯导不断强调电影是生活的还原,以当时台湾的社会氛围,他确实走在时代的尖端,比如《海上花》基本用方言、上海话拍成,即使是现在,以发行商的角度也会认为是有风险的,当然‘侯导’是不理的,他对自己的信仰是贯彻到底的。电影美术也是做到了极致,《海上花》告一段落,我也在想究竟是回去纽约工作还是留在台湾,当然更期待再做一部这样漂亮的作品出来。”当“侯导”提出想拍唐传奇里的女性角色,举了“三红”的故事,红拂、红线、红绡,讲聂隐娘幻逸,合拍武侠,可以先拍这个,要黄文英先找来研究看看。黄文英投入得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还是依着侯孝贤“生活的还原”为原则,只不过从清末上海租界地,到遥远的大唐代,更拉远了时代。侯孝贤起的“三红”开头,很快就幻化成黄文英心里对遥远大唐绚丽的期待,“不禁好奇‘侯导’眼中的唐人世界,会是用何种言语沟通呢?他们如何开始一天的生活?清晨醒来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如何打理妆容、服饰?不同阶级门第的宅邸空间是何种样貌?起居坐卧的榻、案、几、箱、箪笥等家具款式?旅行时马、驴、牛交通车与配备……”
于是从台北出发。台北“故宫”图书馆那些渊博且好眼力的研究员,渐渐也都知道黄文英是来找“唐”的,纷纷出谋划策,比如介绍她去每年为期一个月的日本奈良《正仓院特展》,于是真见识到那些真正来自唐代的生活器物,当年一次又一次随着遣唐使船带回皇室典藏的古物,各种书画、佛经、乐器、生活器具、熏香、服饰、织品、刺绣,稀罕而博杂。
有时一个展览会引领至下一个陌生的国度,甚至一块布料的织染,面料上的汉唐刺绣针法,会引发下一站的旅程。黄文英笑叹,开始没想到一等就十几年。而换个角度看,这又是极幸运的,恐难有第二部电影,可以给一个设计者花在调查考据的过程,付出这样的时间与成本。巴黎吉美美术馆,收藏着来自阿富汗、南亚、东南亚等国的巨型石雕,约略与唐同时期,甚或更早,造型幻奇,恰应了唐传奇中的精怪角色。也在巴黎,她寻来一本描绘印度蒙兀儿王朝沙加贾(Saah Jahan)的古画册,完全合韵去想象唐代胡风古色。古称“花剌子模”的乌兹别克更让人印象深刻:希瓦古城、布哈拉、撒马尔罕各有千秋,乌兹别克在唐代是西突厥人的领域,据说大唐诗人李白就从这里移民长安,当地人仍然保有类似唐人坐“榻”起居的传统,“榻”上置“案”,可以饮酒、弹唱,有时将大榻搬至户外庭院,月光下,盘腿而坐,葡萄美酒,乐舞相合,希瓦古城里有最曼妙动人的胡旋舞!
旅行当下所接触的不见得与唐风尚有任何渊源,当下遇见的人事景物,也不见得立即能对拍摄唐传奇有助益,却也说不定某一天就能派上用场。北印度的阿格拉(Agra)、斋浦尔(Jaipur),以及乌代浦尔(Udipur)、久德浦(Jodhpur)有许多瀚丽的宫殿,现在有些化身为顶级皇宫旅馆,有的转成博物馆,展出历代王储的收藏艺品文物与各种生活器物,极尽奢华富,想象盛世的生活细节就应该是如此绚丽。另外,在印度西北方逻吉斯坦(Rajasthan)有许多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传统市集(Bazar),色彩缤纷、喧闹嘈杂,身历其境,好似入了时光隧道,“明迷光影、芸芸众生”。其中宙哈里市集(Johari Bazar)有许多镶嵌宝石、艳丽多彩的绞结织染与纯手工几何拼贴而成的布毯,美不胜收。尤其南印度Chidambaram Thillai Natarajar与Mahabalipuram两座印度教古寺,距离青奈(Chennai)约数小时车程,古印度朱逻(Chola)王朝时期兴建,自公元六七世纪至今仍香火鼎盛,寺庙外观的雕塑工艺极致非凡,内殿多柱式天顶悬挂一盏盏大型铸铜吊灯,上方油光灼灼闪烁,幽暗中香火缭绕,空气中有股浓浓的异香,恰给予电影《刺客聂隐娘》的内景光影氛围提供绝佳的启发。
当然不全然是旅行,准备《刺客聂隐娘》的里,黄文英也继续与“侯导”合作完成了《千禧曼波》(2001)、《最好时光》()、《红气球》()三部电影。“,才终于听‘侯导’说《刺客聂隐娘》正式提上议事日程。”黄文英告诉本刊。
而这一年,侯孝贤是完全闭关研究唐史。但是显然他有自己的办法和团队保持沟通。“经常会接到他的电话,上来就讲故事。嘉诚公主要从长安嫁到魏博去,原来按照一般的习俗,要坐那个车,羽毛装饰的。可是她嫌那个车太旧,就不要用。后来她的皇兄就给她做了金根车,整个是金子打造的,这本来应该是皇帝才有的规格,可是就给她用了。那以后公主下嫁的时候都要用金根车,打这里来的。回过头来说,田季安的母亲就是这样性格。”朱天文笑说,对于当时正在写长篇小说的自己,田季安、嘉诚公主,还有似懂非懂的魏博,也不过是侯孝贤讲自己就当故事听听,像生疏的外太空。
穿透武侠类型
,侯孝贤就把他手边所有资料和故事都扔给钟阿城、朱天文和谢海盟。卷帙浩繁到令大家都有措手不及之感,挚友相交的默契,确实令他们很快就悟到侯孝贤的心意。“从新旧唐书中找到那些空隙,再从空隙中卡出一个空间,从而把聂隐娘的故事具体成形。聂隐娘本来千来字的文章,但里头讲了魏帅,隐娘是魏博大帅聂锋的女儿,那聂锋又是谁,还提到他的对手节度使刘昌裔,他们之间又是怎样的渊源,这些都好像一个个路标吧,以及时间坐标上有贞元、元和这两个时间点。那就根据这几个小小的路标,找进去,能找出那些历史缝隙之间的人生故事来。”
同样以编剧身份加入《刺客聂隐娘》之中的钟阿城更一语道破。“侯孝贤的聂隐娘故事,就是野史、传闻加想象。重要的是想象,也就是文字的作者是怎么想象的。没有真正的趣味点。只有你想用哪一点来引领故事。聂隐娘中的隐,是一种技能,也就是日本的忍者的忍术,可以译成‘女忍者聂’。这个‘隐’字是可以做揭示性格的文章的。”
剧本工作将近3年,易稿37次。朱天文说,侯孝贤最常讲的还是希望有个时光机器,让他跑去唐朝看一下,“看一眼,我就知道怎么拍了嘛”。“就这一句反复讲、反复讲,但其实现在好多大片拍了唐,可是人家也没这个问题啊。电影对别人就不过是剧情、对白、场景,大家把对白讲讲,这个、那个戏剧性铺一铺,就在这个场景里头做戏剧的表演。可侯导说真想去唐朝看一眼,就知道人物在这个屋子里头平常是在干什么。大家心里都晓得,那是因为侯孝贤电影是把情绪和情感放在日常动作日常生活里面,到‘聂隐娘’,侯孝贤的这些强项、他过往的优势都无法使用了。”朱天文说。
所以在做剧本的时候就尽量做到严整、严密。从前给侯孝贤写剧本,基本就是弄个大概,百分之三五十足矣,然后就留着导演自己到现场看环境有什么再添加,留空间也是默契。“可是这次你晓得如果你不做得尽量严整完备,尽量把这个故事环扣起来,到时候没有就是没有啦,那个现场里没有侯孝贤依赖的真实底子。甚至那个现场也变不出什么东西,比如临时缺个蜡烛缺个烛台什么的,那没法现找一个的,因为每个物件都得推敲,从美术到剧务要照着剧本准备。”
朱天文说《刺客聂隐娘》大概是她做过最像剧本的一个侯孝贤剧本。所谓的严整,第一个最重要的核心是聂隐娘为什么要杀人,凭什么去杀人。于是牵涉道姑的身世由来,她的剑术是怎么回事,凭什么这个师父可以杀人,才推理至聂隐娘为什么可以杀人。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聂隐娘接受她师父的指令去杀这个人,到她不杀这个过程,不仅建立,而且要巩固铺陈这个理由,一步一步看这个武术高强的刺客怎么完成一个杀到不杀的过程。
“侯孝贤始终觉得这两个不成立的话,这电影怎么去说服人呢?先是她杀人这个是从小时候到现在要做的事情,得有个理由。然后为什么一步步偏离杀人的路线,最后就不杀了。从某方面来说,这其实像是做一个选择,然后她为她做的这个选择负责,一个人的故事。而在武侠小说里头刺客杀人是不用解释,过往的武侠讲忠孝节义,还有所谓的侠的东西,是恩仇相报。所以说到底从解释杀人就已是非常不类型的东西,非常不武侠的东西,武侠片是强有力的类型,不过到了侯孝贤,说到底又回到了人本身上来。”
再现唐的想象共同体
另一个方面,朱天文觉得,《刺客聂隐娘》的故事也就是书写某种唐的想象共同体的过程,这就像描绘出《诗经》里的那种中国山水,或是具象化诗词歌赋里的绵绵情思。“其实就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的《想象共同体》,我讲叫‘唐的想象共同体’,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唐,或者是汉唐。这次却是没办法,我们也不知道唐人是怎么生活的、生活细节什么的,所以是每一个人各自发挥所长。”
比如黄文英走遍世界搜罗而来的唐风掠影,结合进具体的人物生活时,钟阿城就是“活的博物馆,活的图书馆”。“东西其实都是装在他的脑子里头。他讲这些东西完全就是信手拈来。等到最开始做的时候,阿城跟我们描述那个器物的样子、名称、用途,我们写进去之后,当然美术组比如黄文英老师,开始做道具的时候还是会去参阅些器物的记载来历,配搭使用。阿城的渊博完全能负担起的是器物、仪礼的部分。”《刺客聂隐娘》里最年轻的编剧谢海盟,是朱天心与唐诺的女儿,从小是在“侯叔叔”的片场长大,曾入围台北文学奖,也是从《最好的时光》开始给朱天文和侯孝贤打剧本,到《刺客聂隐娘》是她的第一份编剧工作,海盟对朱天文也以天文相称,但谈起这些长辈级的工作拍档,言语却仍旧难免钦羡之情。
“亚洲第一影像大师”李屏宾参与进来的时候,就给《刺客聂隐娘》定了大师傅抱石的影调,“傅先生的画简单有力,有点像中国书法那样子,大笔一挥,那些细节却可以很生动,书法写得好的话就像看一幅画一样,而画画又画到书法的境界,也是非常难得。他能画出那种苍茫的大地。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把影像更加神秘化,更具东方的味道去呈现。尤其是我们也尽量避免我们传统近代内地及港台拍的那种极致的唯美。观众对这样子的唯美已经没有感动,那是只有浮躁,没有细节的。”
李屏宾第一次与侯孝贤合作其实是《童年往事》(1985),当时两个人都年轻,作为导演的侯孝贤刚刚为电影圈所关注,但《儿子的大玩偶》、《风柜来者》都是让李屏宾心动不已的电影,于是认定“侯导”是值得合作下去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就常常迫切想了解他在想什么,常常跟他谈,没完没了地谈。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侯导’就不太分镜头了,来了就说我们要干什么,然后你摆一个镜头,他会调整,要不要过去一点、高一点、低一点,跟王家卫导演也很像。”
30年前那个时候流行比较饱和亮丽华丽的灯,不追求那种有情绪味道的质感,只追求每个线条很清楚,每个画面很漂亮,颜色很正常。但《童年往事》里的那个旧时光里的往日情怀,李屏宾和侯孝贤都有亲身的经历,他们对旧时光的感受都不是那样明丽的。所以我就很大胆地放弃了那些专业灯,都用的生活里面60瓦100瓦的灯来拍。“在当时那是很吓人。但是‘侯导’和我都很满意,大家觉得我们是一对怪人,都玩笑说要是男女朋友,就直接可以去结婚了。”
从《海上花》,侯孝贤几乎就把镜头的部分全然交给了李屏宾去掌握,如此“肚子里的蛔虫一般的默契”几乎已成台湾影史上的一段佳话。李屏宾笑说,真的像是恋爱一样,几十年如一日培养着彼此的精神密切。李屏宾很早离开台湾,但几乎每一部电影拍完回来,甚至每次休假回来台湾,都会跟侯孝贤吃饭,完全不是普通的吃吃喝喝。每一次,李屏宾都要问他最近看什么书、看什么东西、准备什么案子,但更多时候,侯孝贤就自己拿书给李屏宾。所以其实电影不是去开会去探讨,而是在生活里聊出来,慢慢去体会,去寻找。“他要拍《刺客聂隐娘》,我也不比他知道得少(笑)。很多年下来,我自己对历史早已非常感兴趣。只是不知道他心中的武侠和心中的魔幻是什么,所以有时候会这样去寻找这个。因为很多人心中有些什么也都不具象嘛,也是要谈才会谈出来,可能有一个什么东西在那边闪烁,不谈它永远是闪烁,谈完之后它就会聚焦了,会有一个最初的方向。”
如李屏宾所言,《海上花》之后,侯孝贤作品几乎没有一部片是雷同的。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脚步、新的尝试、新的冒险。至《刺客聂隐娘》,侯孝贤甚至想过全片用16毫米新闻胶片摄影机完成,拿旧时纪实新闻片的粗粝风格和中式武侠的幻逸洒脱来个杂交实验。当然,最终16毫米的粗粝久远感只落在了隐娘回忆的段落,电影全片由35毫米拍成,算是种温和的解决。李屏宾笑说侯孝贤是那种只要地球上还有一尺胶片,就会想办法拿来拍成电影的人,他对影像质感的追求,几乎可以贯穿到拍电影这个动作本身。
“当然在这点上我们也是非常一致。我们的年代,学拍电影就像写毛笔字。你先要会坐、会拿笔,然后很长时间我们才写一个‘永’字。永字每一撇每一捺都有学问。现在大家拍数字影像,就像拿签字笔圆珠笔,拿了就可以写。从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写一个字嘛。只是用原子笔写不需要很多的时间去准备和沉淀,好似还更方便。但对我们而言,起码乐趣不在了,某种意义上是损失了很多本质,目的可能是一样,但是本质没有了。我们都要个电影的本质。”
风格之外,再现“唐的想象共同体”,细枝末节也全是关键。《刺客聂隐娘》的拍摄场景主要分三块:外景部分在武当山开镜,转往神农架,又转场内蒙古;内景则是在台湾宜兰搭设一座壮观的“聂府”;内景与外景相容的部分则全拍在日本。首先是影像风格要统一,进而再保证那个唐的想象共同体里的方方面面,毫发无损齐备周全。“我们要粗粝而苍茫,并不是不要细节,全片最华丽的大殿部分反而用很极简的灯光来处理,因为美术组的布景全部都是一层层的纱,如果灯光全部打足会破坏那些布景质感跟细节,纱都白掉了,所以基本上又用了很多日光灯当光源,很微弱的光让那些细节都保留下来。类似需要照顾到的细节之美在这一部片子里尤其多,我们就不急,慢慢拍,拍了4万多尺。”
隐娘,孤独而淳执
“聂,就是三个耳朵,所以就是一直听,隐娘在树上,听万千声响,时机一到,飞身而下,独战群敌。”侯孝贤说自己从大学时代起,心里就有了这个画面,那是《刺客聂隐娘》的起点,只是一直以来他觉得武侠是难的,想拍却又拖沓。到如今李屏宾玩笑说,侯导68岁,于是拍出了一部走在地上的武侠。“每次吊个树他都要看合不合身体逻辑。当然我们也拍了些功夫是超越了普通人的能力,练功的人可以达到的那些突破,但像通常武侠片的呈现,比如飞檐走壁,侯导根本不会接受。起初我们也试着拍了有几场更加精彩的动作戏,但拍着拍着就觉得那些是不属于侯孝贤先生的嘛。加上舒淇恐高,没法控制就露出些惊恐神色,侯导索性就叫她在地上走,孤独地走,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都是在跟着走。生命在往前去,时间一直逝去。后来我反而觉得走就是表达的情感。”
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剪辑师廖青松、廖桑的印象里,同样是开场这场标志性的动作场面,聂隐娘奉师命去刺杀大寮,既然拍了那些动作场面的招式,最初侯孝贤和廖青松也曾想要照着一个武侠的概念去完成剪辑,可是试过之后,觉得说毕竟不是拍武侠的导演,那种市场上的武侠片套路拿来,说不出哪里奇奇怪怪。
索性,侯孝贤就此给全片的剪辑定下了唐诗的节奏,用影像书写诗意,也就是打破常规剪辑的连续性,跳切、停顿,单独放大独立的单一画面,形成诗一般的韵和律。“所以那段动作场面反而用的是诗性的剪法,刀光剑影,人物动作不是正打反打的规律,反而是落叶纷纷这样的独立画面被有意延长,有跳跃,有停顿,也有照应和工整。在我看,从来没有一部武侠电影这样剪辑而成。”
初剪用了半年时间,朱天文看了,觉得是她和侯孝贤合作30年以来最沮丧的一次看片。最大的问题是聂隐娘不见了。她的情绪、她的存在被她周围的故事彻底盖起来。侯孝贤却气定神闲,开始剪辑第二版,每天不过下午去剪上几个小时而已,耐下心来不断看,却又不过于进入其中。“第二剪是重新从情绪角度疏理聂隐娘的存在,导演重新找出那个聂隐娘来。”廖青松解释说。
时隔9个月,朱天文再去看片,讶异于如今电影里的聂隐娘跟原先剧本上的聂隐娘完全不同了。“剧本上的聂隐娘是很聪明,先人一步,永远是在冷眼看世界的。如今剪出来的聂隐娘木讷寡言,有点傻傻的、愚执,好的事情总是轮不到她,可是那些坏的事情全部都推给她,她被牺牲于政治运作了,现实里头容不下她,被道姑带走,后来她回来,目睹的是她缺席的、她的回忆,她以前念念不忘的嘉诚公主,教她弹筝,牡丹花、嘉诚公主代表唐朝那种‘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最繁华一面,可也说不见就不见了,更要紧的是再见到曾经的青梅竹马,却负师命要取其性命。”
那次看片,朱天文一口气看了两遍,看到第二遍,她觉得自己的眼睛有点湿湿的,她说自己禁不住心疼起如今的这个聂隐娘。“这个隐娘是有一丝淳执的,或者这是舒淇身上隐藏的东西,侯孝贤终归还是把人的底子展现出来。你老看到舒淇在走路,一个人走,孤单单地走,而舒淇走路又有一点点外八字,这么一个武功高强的,走路的背影却是有一点外八字的,就觉得她其实是一个很结实的人,并且是有一种结实的素朴的善念,这解释了一切,反而我们刚开始设定的那些从杀到不杀的一些理由,到此就都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