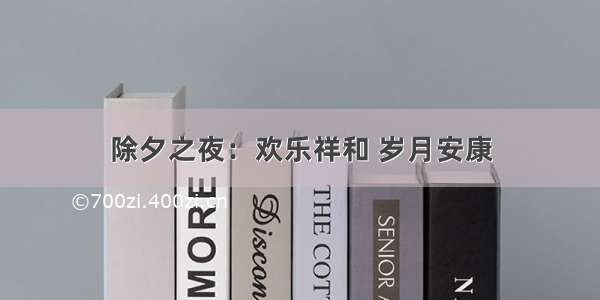作者简介
鲍国华,天津市人,2002—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王富仁教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师从陈平原教授。现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鲁迅研究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是一篇鲁迅演讲的记录,后经作者多次修改,目前存世的有多个正式发表的文字互异的版本。由于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鲁迅在演讲中不时表现出对现实的介入,于论学之中包含讽世之意。这一点不仅得到鲁迅本人证实[1],也为读者熟知。尽管不是一篇纯粹的学术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仍体现出鲁迅的文学史研究观念,可以视为鲁迅未完成的《中国文学史》的魏晋部分。[2] 而且,鲁迅透视现实并独出新见,正是以深厚的学术修养和卓越的文学史识见为思想基础;于论学中寄寓现实体验和社会批评,也是鲁迅后期一个重要的言说策略。本文拟采取读书笔记的形式,以考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学术价值为出发点,分别围绕该文的版本及修改、与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学术关系以及该文体现出的鲁迅的文学史观等问题展开论述,力图凸显该文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中的地位和意义,以及鲁迅文学史观的独特价值。
一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是鲁迅于1927年7月23日、26日在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广州夏令学术演讲会上所作演讲的记录。记录者署名为邱桂英、罗西。邱桂英是当时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学生,罗西即长篇小说《一代风流》的作者欧阳山。[3] 这次演讲由两人记录整理后,经鲁迅本人修改,连载于1927年8月11至13日、15至17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173至178期(以下简称“记录稿”)。同年,经鲁迅再次修改,发表于1927年11月16日《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2号(以下简称“修改稿”)。该文后辑入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10月出版的《而已集》,编辑过程中又经鲁迅进一步修订,成为作者生前的定稿(以下简称“改定稿”)。至此,《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经鲁迅多次修改,出现了三个正式发表的文字互异的版本。鲁迅逝世后,在1938年、1956至1958年、1981年和四次出版的《鲁迅全集》中,该文又经编者修订,文字和标点有所改动。在修改稿中,鲁迅订正了记录稿中明显的错字和脱衍,如记录稿“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本朝的人物”,修改稿改作“这就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增加的“恭维”二字显然是记录稿中的脱文。此外,鲁迅还给文章加了副标题,并对文字和标点进行了大量增删,如记录稿“汉时大家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有改变,便吃开头了”,修改稿改为“汉时,大家除治病时万不得已之外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起来了”;记录稿“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故我想,衣大,穿屐,散发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教育实在无关的”,修改稿只保留“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一样”一句,删去了后面的文字。在这些修改中,有的是对记录稿中表达不够清晰之处的订正,如记录稿“因为已经做过工作”,修改稿作“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添加“有人”二字,句意更显完整,这些改动在改定稿中都保留了下来;有的则是在记录稿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如记录稿“此外,他喜谈也喜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吃药”,修改稿作“他身子不大好,此外也许还有点荒唐的事情,因此不能不吃药”,这些发挥在后来的改定稿中大多恢复了记录稿的原貌。在辑入《而已集》的改定稿中,鲁迅除继续订正标点与文字的错讹外,还将修改稿中的多处发挥还原为记录稿的原貌,以尽量保持演讲的本来面貌。如上引例,改定稿作“此外,他也喜欢谈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仅调整了记录稿中错乱的语序,并将“吃”改为“服”,删去了修改稿中的发挥,文字大体上恢复了记录稿的原貌。改定稿作为鲁迅生前的定稿,在校勘和修订上更为用力,不仅填补了上一次修改中的遗漏,如记录稿“所以他帷幄下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修改稿与记录稿相同,改定稿则改作“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帷幄”意为“军队里用的帐篷”[4],用“里面”显然比“下面”准确,一字之易,却得见作者之细心;而且在一些修改稿中已改动的地方,鲁迅又做了进一步的修改,使表达更加完整、准确、清晰,如记录稿“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要求”,修改稿作“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乞求”,改定稿则易为“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修改稿中以“乞求”易记录稿中的“要求”,已较之后者贴切,改定稿进而易为“求乞”,更为恰当地表达了语意。又如记录稿“曹操曹丕以外,下面有七个人,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修改稿作“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七个人,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文字和标点只有小改动,都没有详细列举“七子”的姓名,改定稿作“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增补了七人的名单。据上可见,鲁迅对《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先后三次修改,对文字和标点要求十分严格,体现出严谨、扎实的态度。
二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鲁迅明示以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为参考文献,称刘著“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5]然而,鲁迅对刘著的态度,决非仅仅视之为材料汇编这么简单,刘著无论是在学术思路还是在一些基本论断上均对鲁迅产生重要影响。刘师培与鲁迅的学术联系,近年来已有学者详细梳理。[6]《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采取罗列古籍中的相关材料,后附案语的论述体例,似乎有“论”而无“史”,而这恰恰是刘师培文学史观的体现。在《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一文中,刘师培提出“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的论断,并提出以《文章志》和《文章流别》作为文学史的论述体例。[7]《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即为这一文学史研究思路的呈现。《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开篇即提出“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8]的主张,以中国古代文论中“文”的概念作为文学的中心,将“笔”摒除于外[9],一方面与晚清以降的“桐城派”文论相对举,另一方面又明确针对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体系,力图在中国文论体系中立论。可见,刘师培在立论之初,具有明确的文学史研究意识,这使其研究异于中国古代的“文笔之辨”,显示出创建独立的文学史研究模式的努力,而对论述体例的选择,则成为这一努力下的自觉实践。因此,《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论述体例,表面上近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章辨体”和“文章流别”,却因作者“对文学史的自觉”这一写作前提,成为探索中国式的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模式的可贵尝试。鲁迅曾师从章太炎,但其文学观却更接近刘师培。据许寿裳回忆,章太炎一次向鲁迅问及文学的定义,鲁迅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章太炎对这一回答并未予以认可。[10]鲁迅对文学的定义,近于刘师培的观点,这影响到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的一些文学史论断。例如,鲁迅视魏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与刘师培的论断十分近似;而将这一时代的文学特色断为“清峻,通脱,华丽,壮大”,与刘师培“清峻”,“通侻”,“聘词”,“华靡”的论断大体一致,从中不难看出两者的学术联系。然而,问题似乎没有这么简单。鲁迅与刘师培的学术关系,并非影响与被影响这一结论所能涵盖。一方面,尽管鲁迅的文学观与刘师培相近,却并不一定是在刘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由前引许寿裳的回忆可见,正是鲁迅自身的文学观念,促使他认同刘师培的有关论断,并吸收到自己的研究中,而不是在刘的影响下选择了这一文学观。可以肯定的只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有关魏晋文学历史地位和文学特色的若干论断,受到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影响。另一方面,鲁迅治学与刘师培相近处,如采用清儒家法,注重史料搜集;撰文学史从文字论起;以时代精神作为分析文学风貌的依据等等,或服膺清代朴学家的治学理念,或以阮元《文言说》为论文字的理论依据,或秉承《文心雕龙》“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文学史观,只能表明二人有相近的学术资源和治学理念,不能单纯断定为“刘影响鲁”这一结论。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开篇,鲁迅指出在论述过程中对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略其所详而详其所略。我以为,鲁迅此举不仅明示对刘著观点的借鉴以及对前贤著述的敬意[11],而且在这详略之中,显示出二人文学史观的差别。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鲁迅并不着力于对具体作家作品或文体流变的分析,而注重一个时代的政治环境、社会风尚以及文人心态等文学外部因素,着力于穿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透视时代的精神。而这正是与以文体为中心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详略区别所在,且与通常的文学史研究思路大相径庭,更近于今人眼中的思想史、文化史和文人心态史。这恰恰体现出鲁迅对文学史这一研究方式的独特理解,促成鲁迅的一系列文学史著述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与写作中的地位和价值。综上所述,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对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影响确实存在,不能忽视,但也不宜夸大。刘师培和鲁迅,并不是一个历时性存在的思想发展脉络中相继承、相衔接的两个关节点,而更体现为思想的共时性关系,即在思想激荡的晚清至“五四”,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共同问题显示出的相近的思维方式。对于鲁迅这样一个思想个体而言,古今中外一切文化传统和思想资源只有植入鲁迅独立的思维世界,经过这个世界创造性的整合才能成为其思想质素。鲁迅不会因为任何一种文化传统和思想资源的影响而成为鲁迅。同样,任何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思想个体,只有其自身才能成为实现这一独创性的决定因素。鲁迅与刘师培的学术关系进一步证明以下论断:“一种创造性的文化成果必须经过特定个人的主观想像力和独立的思维过程才能被实际地创造出来,它不仅仅是已有事物的自身连接或重新组合。”[12]
刘师培
三《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问世后,其研究思路和学术论断一直受到文学史家的推崇,特别是鲁迅对文人心态的分析和时代精神的透视,常为后世研究者所称赏和引用,成为魏晋文学研究的经典范例,至今无人超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学术成就,除与鲁迅深厚的学术修养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密切相关外,更由鲁迅独特的文学史研究观念所决定。《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与今天的文学史形态迥异,近于今人眼中的思想史、文化史和文人心态史,这正是鲁迅文学史观的独特之处。在鲁迅看来,研究人类精神生活和精神产品的文学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等并无明显分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开篇即明示是“文学史上的一部分”,并以“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为最基本的研究依据,既是对刘勰“时序”说的继承,又充分体现出鲁迅本人对文学史独特的观察和把握方式。鲁迅文中称:“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我以为,这句话对理解《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和鲁迅的文学史研究思路颇为关键。鲁迅的文学史研究,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世态人心的透彻把握,据此进一步透视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其发现常出人意表,道他人所不能道,而又准确贴切,令人折服。即使是对文体及其艺术风格的分析,也每从社会思想和文人心态入手,颇多知心之论。如对汉末魏初文风的评价,鲁迅即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文化风气出发,指出居乱世尚刑名立严法,为治世反清流斥执拗,遂促成文章清峻、通脱的风格,并据此肯定曹操的才能和功绩,从而将思想史、文化史与文学史相融会。鲁迅之所以不将文学史与思想史、文化史截然分界,恰恰是因为它们都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究方式,需要对世态人心的强烈关注和深入观察,而维系它们的纽带正是“人”,是鲁迅终其一生的“立人”思想。自1906年中断在仙台医专的学业,转向文学启蒙以后,“人”的概念开始引起鲁迅的关注。这一概念及其不同表述方式逐渐成为鲁迅著述中的一个关键词。与此同时,出于对中国现实的强烈关注和民族危机的深切忧虑,“立人”成为鲁迅思想方式与文化行动的基点,并进而成为鲁迅整个精神世界的核心。[13]而作为鲁迅精神世界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研究,“立人”思想也一直贯穿其中,成为鲁迅文学史研究的逻辑起点。基于“立人”思想,鲁迅在文学史研究中首先注重对世态人心的透视,由“观人心”的角度立论,从而在人所共知的研究材料中见他人所不能见,得出新颖且令人信服的结论。即以常被后世研究者称道的对嵇康阮籍的评价为例,嵇、阮二人一直以反礼教的姿态为人熟知,亦因此而为人诟病。鲁迅却认为,他们的反礼教,实际是太爱礼教之故,是因为痛感魏晋时人以崇礼教为名,实则毁坏礼教的风气,激而变成反对礼教。正是基于“立人”这一文学史研究的逻辑起点,才使得“人”成为鲁迅文学史关注的中心,把握文学现象的基本尺度。《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充分体现出鲁迅独特的文学史观念——“人史”观。晚清至“五四”的特殊历史境遇使文学担负起摆脱民族危机,实现精神自救的重任。“五四”时期对“人”的发现,更是通过文学获得,又通过文学记录和传播。这使文学得以居于现代中国思想界的灵魂地位,表现为大规模的思想运动首先以文学运动的方式展开。在中国文学史上,就“人的文学”这一命意而论,“五四”新文学当为翘楚。而作为学术研究的文学史,亦以“人”的确立为最终指向,使“人的文学史”的理念植入“五四”以后文学史的精神质素之中。鲁迅在这方面既有开创之功,又是最坚定、走得最远的一位。包括《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内的一系列文学史著述,既保持了严谨扎实的学理性,又时时与现实人生紧密相关。可见,通过文学史研究实现对“人”的关注和把握,实现对现实的参与是鲁迅学术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应该承认,鲁迅深厚的学术修养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其文学史著述具有很强的学理性。但是,学理探讨只是他思考问题的路径,却决不是他思考的终点。同样,鲁迅论文学史时迭出新见,也不是仅仅从若干研究材料中得来,而恰恰是对文学史的独特思考,使他能够对普通材料做出新的诠释。鲁迅的学术研究,更鲜明地体现为强烈的主体参与意识和深入的现实关怀。这也是鲁迅异于同时代文学史家的独特之处。在文学史研究中,鲁迅以“人”为中心,时时以己心照人心,又时时以人心观己心,实现了对人心的深刻洞察,又鲜明地凸显着一个自我的存在,这是一个时刻关注国家、民族、社会乃至整个人类命运的思想者的主体精神,是一种强烈的现实感受和朴素的人间情怀。鲁迅以“人史”作为维系文学史精神价值的命脉,从而真正实践了“文学是人学”的主张。
注释:[1] 鲁迅在1928年12月30日致陈濬信中说:“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志大才疏’,哀北海之终不免也。迩来南朔奔波,所阅颇众,聚感积虑,发为狂言。”《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46页。[2]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五·杂谈著作》称“鲁迅想要做的《中国文学史》”的魏晋六朝部分的标题是“酒,药,女,佛”,“他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便是这部文学史的一部分。”见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253页。[3] 欧阳山:《光明的探索》,见马蹄疾:《鲁迅演讲考》,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5-247页。[4] 据《现代汉语词典》释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版,第1195页。[5] 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第502页。以下引用该文,均据此版本,不再注明。[6] 这一课题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见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杰:《鲁迅与刘师培的学术联系》,《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6期。[7] 刘师培:《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见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页。[8]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第3页。[9] 刘师培的文学观,参见王风:《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见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0]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七 从章先生学》,《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第231页。[11] 刘师培生于1884年,比鲁迅小三岁,但其革命思想和学术成就均先于鲁迅闻名于世,得与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晚清学者同列。[12] 王富仁:《鲁迅与中国文化》,见氏著:《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13] 参见钱理群:《以立人为中心——鲁迅思想与文学的逻辑起点》,见氏著:《与鲁迅相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
本期编辑:馮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