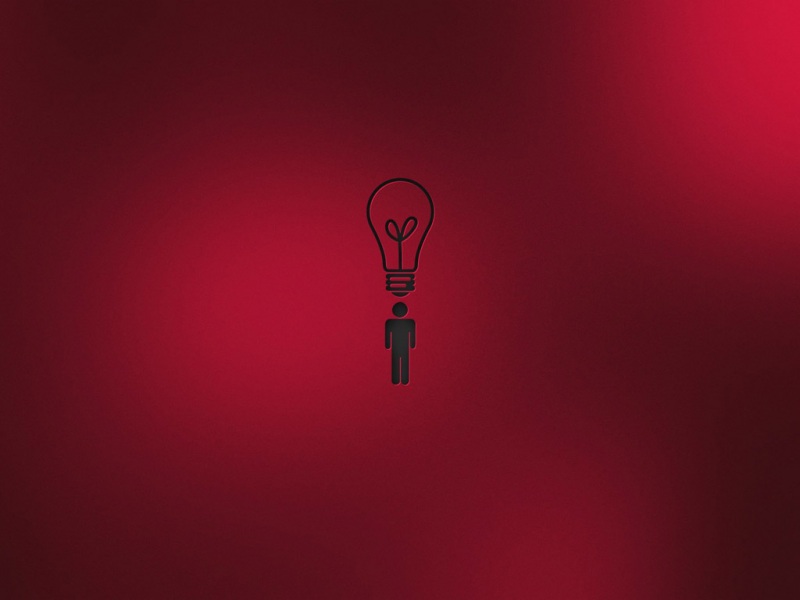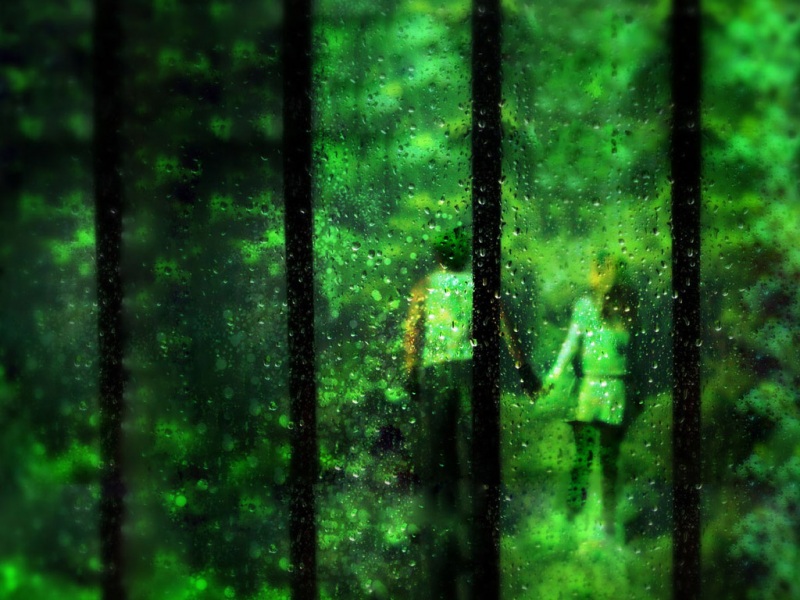午夜梦回。管新生以为自己还在厂里。
刚刚一轮中班上好,衣服上还留着熔铸车间熔炉烘出的温度。吆五喝六地与工友骑自行车下班,暗夜里沿着铝材厂所在的眉州路一直骑到控江路黄兴路口。那个路口的昏黄路灯下,有个小酒铺,是工人们下班后回家前的聚点。他们的嗓音很远就能听到。笑声与动静,交织成一片剪影。那些深蓝色的厂服,锃亮的老坦克龙头,和他们将要归去的工人新村,都是那个火红的年代里,最令人艳羡的身份象征。
做工人去,到工厂去,住进工人新村去。那个时代的浪潮改变了管新生,也影响了千千万万上海家庭的命运。
虽然如今66岁的管新生已经离开工厂多年,现实中的上海铝材厂的2.5万平方米建筑两年前已全部拆除完毕,当年一起干活饮酒的工友或早早退休,或已下岗多年,但留在管新生心里的工人情结还在。他和女儿一起花费写了小说《工人》,只因他难忘,“1968年就进厂工作的青春”。
但也许,一切要早于入厂工作那个年份。从1954年那个傍晚全家迁入控江新村开始,工人的印记就烙在了管新生的血液里。从那一年开始,工人的身份,成为管新生识别自己、观察城市的视角。
一个普通工人的家
1951年起,上海市政府在接近沪东、沪西工业区周边的控江路、志丹路、曹杨路、天山路、沪南的大木桥一带规划了9个住宅建设基地,先后建造了曹杨新村、控江新村、长白新村等18个工人新村,解决了一批工人家庭的住房问题。最早,只有劳模、先进工作者才有可能分到这里的房子。1954年《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在一个炼钢工人的家里》,描述了当时记者走进工人新村的所见所闻:
“控江新村在上海市郊江湾。村子内,到处栽着嫩绿的小树,一位亚细亚钢铁厂炼钢工人的家就住在这个"新辟花园’内。一进屋子,右边可以看见整整齐齐的专用厨房,左首是清洁的盥洗室。楼上两间卧室也收拾得妥妥帖帖。洁白的墙壁,光滑的地板,明亮的玻璃窗前还有一幅漂亮的花布窗幔在迎风飘拂。房子内的桌椅、衣橱和双人床全是新的; 一只新买的台钟不知疲倦地在为屋子的主人报着时刻。”到了午饭时间,记者“坐上餐桌,看见桌上摆着这样几种菜:肉丝蛋汤、茭白炒虾仁、青菜,还有满满一碗红烧肉饼。”远处“另一个工人家庭的卧室:里面有崭新的家具,窗前挂着绯色的窗幔,一只五斗橱上还安放了一瓶鲜花……”工人们争先恐后描述了解放后翻身做主的欣喜之情,以及对未来的期许。
也是1954年,管新生一家从常德路的弄堂房子搬迁到杨浦区的控江新村。这一年,他5岁。
给弄堂顽童一个下马威
1954年十月的一天,管新生的父亲埋头弓腰拉着一辆很大很长的劳动榻车(一种双轮平板人力车),车上坐着管新生、他的奶奶和妈妈,妈妈怀里抱着小弟弟。从普陀出发到杨浦区双阳路,一直到了傍晚时分,这个工人家庭终于进入了象征着新时代工人地位的控江新村。
房子是三层楼工房,每一楼面四户人家,1室2室3室均为一室户,4室为内套的两室户,走廊里两个卫生间、一个浴室供公用,一个大灶间里四户人家的煤球炉(后来则为煤气灶)倚墙而立,外面还有一个七八平方米含一个水斗的公共阳台。房费也很便宜,管新生家所住的是一居室,使用面积大约是13.9平方米,房费仅为每月几毛钱。
就在大人们一惊一乍参观的当口,管新生已经不甘寂寞地奔出屋子到外面一个人“白相”去了——直到天色已暗才想到了回家。可满目尽是一模一样的三层楼尖顶房子,无论奔跑到哪里,眼中景色不变:三角屋顶,三层楼房,三面草影,宛如迷宫。最终当新村里燃亮了电灯的时候,管新生聪明地想起自己的家应该在东边某幢楼的三楼。看到有灯亮着的房子,便找了上去;灯不亮,便拐向另一幢。
就这样,几经周折,他终于找到了家——家中的灯下,只剩爸爸一个人,奶奶和妈妈则去寻找失踪的孩子了……要是回到弄堂时代,肯定不会如此这般狼狈地找不到家门。
后来他想:也许,这就是工人新村文化给初遇的石库门文化一个小小的下马威吧。
命运各异的邻居们
“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的顺口溜,描述了上世纪50年代工人们对工人新村的向往。
许多沪东地区的工人在解放前都是“住在阁楼上、亭子间、草棚子里的”,能住进整齐有煤卫设施的新村,都觉得面上有光。不过,工人新村的住户也不全是清一色的产业工人。与管新生住在一个楼层里的其余三户人家就各有特色。
其中一户的男主人是商店店员,直到“文革”之前,一直保持着西装革履大背头的打扮,其日常爱好是写诗和读报上的诗歌。每每清晨,听见同层共用的厕所里,传来抑扬顿挫的读诗声,那就是店员在如厕了。另一户居民是富裕家庭,户主老头写得一手好字,当时在居委会的图书室誊写书籍名称、记录借阅情况。
一夕“文革”开始,一天店员狼狈地逃回家,裤脚管被剪坏,脖子上挂着被损毁的皮鞋。而富裕人家的老头被叫到里弄里上台接受批斗。每次开会,管新生当然也跟着去喊“打倒地主”的口号。但心里总很疑惑,眼前慈眉善目的邻居和书里写的凶神恶煞剥削阶级并无丝毫相似之处。
1968年,管新生初中毕业。“一片红”前夕,他得到上海铝材厂消息,自己将进厂做工。
后来他才知道,当时厂里主管人事的人,在档案中看到管新生住在控江新村,便问也住在控江新村的儿子是否知道此人。儿子答“一起白相到大的”。如此一来,基于某种类似于同乡保荐的认同感,在工人新村长大的管新生没有上山下乡,而是跻身当时城中最光荣的阶层——成了工人中的一员。
回不去的年轻时光
1974年,阿尔巴尼亚中学生青年足球队在上海访问期间,参观的地方中,就有控江新村。到了1977年,日本田径团访沪,也参观了控江新村。控江是那个时代新中国乐意向外国友人展示的幸福生活样本。
住在象征幸福新生活的控江新村里的管新生,也开始学着写小说和散文。1971年,他在《解放日报》 发表散文诗《炉工之歌》,所写的,也是对自己当炉前工的生活描述:“披一身霞光,挽万顷狂澜,咱手舞钢钎,不论酷暑严寒,出没在硝烟里,战斗在熔炉前!”凭一支笔,几年后管新生借调到作协搞创作。但每个月,他还是雷打不动回厂报到——去履行在厂报上签字的主编职责,去和班组里的工人兄弟海吹神聊大杯喝酒……没有人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失去铁饭碗。
等到下岗潮袭来,许多昔日的伙伴都被甩出原有的生活轨道。管新生自己的妹妹、妻妹等亲属,也不得不在人到中年时再谋出路。当然,管新生也在后来的采访中,了解了许多在下岗工人中涌现出的大老板和经营有方的私营业主,他们逐步购置新的商品房,渐渐远离了工人新村。
但每每走过控江新村,看着窗户里隐隐约约出现的人影,管新生的心里还是会一阵亲切。他知道他们都拥有做工人的记忆。那些激荡人心的岁月还是会回到他的心头。他依旧想念着在熔炉前的时刻:下了班后把汗湿的外套甩上肩头,携着工友们去澡堂,那都是割头不换的兄弟,也是他回不去的年轻时光。
(作者:沈轶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