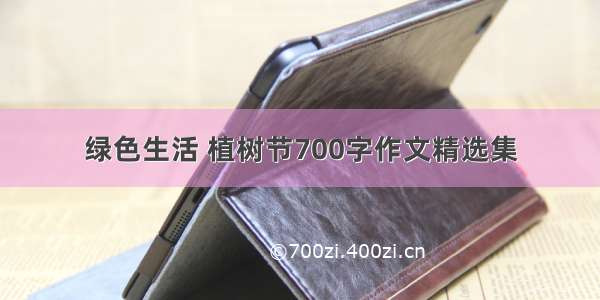这是STORYBOOK上的系列故事
插 画 / 安 娜
生活在这条小胡同中的人,每天都经历着亲情、爱情和友情的考验,面对复杂情感带来的种种困扰,每个人都有最不为人知的一面,或是自私,或是嫉妒,或是憎恨。
随着时日的推移,在成长的道路上,胡同内的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从未有过的羁绊和缠绕,对自我、对爱、对世界的认识有着微妙的变化。
他们不仅是活在故事里的人物,更是现实世界里我们的缩影。
《胡同纪事》第10篇兄弟
壹
沈勉再度踏入这座小楼时,已经是和五年前截然不同的境地。
有句老话叫“人生无常”,沈勉春风得意时常把它挂在嘴边,权当糊上一层自谦的粗劣面具,是生意场上惯用的客套话,没料想如今真应到了他身上。
他沉默地推开挂满铁锈的沉重大门,门轴“吱呀”的声音刺进他的耳朵,这房子有太久的年头,在沈勉算不得快乐的童年回忆里,它连同这刺耳的吱呀声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就连铁门上被雕成貔貅状的门环也斑驳着记忆中的铁锈,这一度成为沈勉不愿踏足老房子的重要原因之一——这老东西仿佛有什么魔力,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所有踏足此处的人都蒙上一层经年的灰尘,泛着旧日不令人喜悦的霉味。
那些旧日或许是某些人的高光时刻,是阖家欢乐的好光景,但却是沈勉最为糟糕的年岁,他记得自己当年的模样:一米六都不到的个子,瘦得像一株长在石缝间的植物,再多的雨水和阳光都没能让他长得茁壮。
单单是这些也就罢了——沈勉带着点怨念,穿过宽敞又短促的门廊,手上拎着仓促而就的行李,紧踏两步,站在客厅同样破败的铁门前,等待着陈年的思绪翻腾上胸膛。
单单是瘦弱,沈勉觉得也就罢了,在农村的那几年,哪家的小子都是一副营养不良的饿鬼样,春天时呼啦啦地跑进村后的树林,蝗虫过境一般将所有能塞进嘴里的东西通通嚼吃入腹。
可一离了家,坐上开往城里的陌生汽车,颠簸两小时后,便横插入一个沈勤,坦荡荡地迈进大门,皮肤被正午的阳光曝晒成古铜色,已经窜到了一米七,脚上踏着沈勉根本叫不出名字的球鞋,手里抱着一只脏兮兮的篮球,笑眯眯地经过他身旁,弯着脑袋任由沈母带着疼爱将他脑门上的汗系数擦去。
沈勉靠着当年尚且洁白的墙,脚跟与墙缝小心对齐,对着脏兮兮的拖鞋沉默半晌,无声地动了动脚趾,尔后抬起头打量这一幅其乐融融的场面,沈勤背对他站着,沈勉的全部注意力便放在了沈母身上。
她遗传给两兄弟一副天生的好容貌,眉毛弯弯,脸如白玉,眼里溢满笑意,抬手擦汗的动作那样轻巧温柔,沈勉觉得就连隔壁大娘供佛时也不如她这般的虔诚小心。
沈勤转过身来,整个人逆着光站着,每一根发梢仿佛都挑着一缕阳光,沈勉迎着太阳抬头看他,眼睛被阳光刺得酸胀。
“沈勉?”沈勤笑着回头向沈母确认,尔后转过身,漫不经心——最起码在沈勉看来是漫不经心,拍了拍他的肩膀:“以后你跟我住东边儿。”
他抬起下巴,冲一间屋子努了努嘴,便抱着篮球轻巧地绕过他,扬手将篮球掷进了院子角落里的一口大缸里,那里头蓄着经年的雨水,常年泛着沉重的绿色,球重重地砸过去的瞬间炸出一圈水花,有那么几滴不偏不倚地溅在沈勉的身上。
沈勉扭过头,看了看院子的一角,那口缸果然还杵在那里,缸底一圈已经爬满了青苔,夏天的时候雨水充沛,水里会悄无声息地长出成群的不断在狂舞的细长虫子。
他也是过了许久才知道,那些是蚊子的幼虫,生在水里,汲取养分迅速成长为新一轮的麻烦,一代一代,经久不息。
等他修养过来,第一件事便要一锤砸烂这笨重的陶缸,叫那些蚊子再不敢打这户人家的主意。
贰
沈勉掏出沈勤交给他的钥匙,不太熟练地插入锁眼,正反试了两圈,才用力将门拽开,提着行李走了进去。
房子被人仔细收拾过,没有他预想中灰尘漫天的场景,沙发上的靠垫摆放得整齐有序,只有一方空落落的茶几显得有些突兀,屋子一角摆着一架有些年头的旧钢琴,上头盖着暗黄色的钢琴布,曾承包了如今在外定居的妹妹儿时所有的快乐。
这房子算不得大,比着沈勉抵押出去的那一处住所还要小上几十平方,然而三室两厅的构造曾塞了一家六口,也并没让人觉得拥挤。
沈勉环顾四周,勉强在东边儿的承重墙上找到了自己曾在这里生活过的证据:已经泛出暗黄色纹路的墙角,刻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小字,那是沈勉回来后不久留下的唯一作品。
这房子现如今归在了沈勤的名下,二老去世后沈勤操办了所有后事,将丧礼均分了,留在城郊的一处房产变卖后均给了兄妹四人,沈勤拿了最少的一份。
沈勉最看不上的就是他这样的做派,明明是该一分一厘算清楚的关头,他却偏偏要当着众人的面假装自己吃了亏,以换一片虚心假意的夸赞,其实到头来没人会记得他曾让出的好。
人生在世,谁不是只惦记着自己的好处,只有他揣着一颗时时刻刻想要感动别人的“菩萨心肠”,吃一堑永远也没长一智。
话虽这么说,出事的那天晚上,沈勉在一片混乱中还是下意识打给了沈勤——无论如何,他毕竟是自己的亲兄弟,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交情,比那些生意场上的狐朋狗友到底是不一样。
沈勤没叫他失望,接到消息就连夜坐火车从家里赶过来,上下打点好几天,才终于将沈勉从号里弄出来,颠簸数十个小时,终于将沈勉毫发无损地弄回了家。
沈勉对此并不觉得感谢,也无什么愧疚,他满心挂扯着山一样的外债,愁得油米不进,蹲监的这几天几乎将他所有的精神都拖垮,下火车时已经是强弩之末。
沈勤转过身擦擦沾了几滴隔夜泡面汤的眼镜,将眼镜腿捏在手里,皱起眉头看他:“回家一起吃个饭?”
他指的自然是自己的一家三口的家,沈勉眼角抽了抽,绷紧的神经一下子垮下来,压得他有些想吐:“不了。”
说完他便有些后悔:他所有的身家都安置在了数千里外的城市,在这座名义上的家乡并无半点安身立命的东西,甚至连早些年乡下养父分给自己的一小块地也因为嫌麻烦转手送了人。
“我住——”哪怕是住旅馆也行,沈勉心想:他不想这一生所有的狼狈时刻都有一个沈勤站在身边,这只会叫他更加自惭形愧。
沈勤仿佛他肚里的蛔虫般未卜先知,变戏法般掏出一串钥匙:“这样,老院一直空着,你先回去住两天,其他的事情过两天再说。”
沈勉心里被刺了下,接过钥匙沉默半晌,只灰着一张脸,握着沈勤给他的钥匙,慢慢地朝记忆中的方向走去。
他其实已经许久没有回到过这座小而拥挤的城市,火车站周围他曾熟悉的一切如今全然是陌生的门脸,可冥冥之中仿佛还有什么指引着他,叫他迈开步子,拐三个弯儿,再等两个不长不短的红灯——一步都未曾走错地摸到了巷口的老房子前。
老房子还是那样,沈勉的离开与归来于它而言只是件无关痛痒的小事,橘红色的墙漆铺展开来——依旧如沈勉记忆中那样扎眼。
他揣着几分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挑剔,关上房门,走到正对着客厅门的供桌前伸手摸了一把,意料中的干净——沈勤有着大多数医生都有的臭毛病:轻微的洁癖,这供桌不必说也是他的杰作。
沈勉对这栋老房子所有的记忆不过是童年时的几个模糊片段,不像沈勤和其他几个兄弟姐妹般,将老房子视作逝去的父母,清明忌日都要回来郑重其事地磕上几个响头,再絮絮叨叨说上一些永无人回应的家长里短,最后凑在一桌吃上一顿寡淡的家常饭。
沈勉尤其看不惯这样的做派,索性找足借口不予参加,倒也没谁有什么意见——那是他还财大气粗的时候,又远在大城市做着动辄几十万一单的“大生意”,理所应当比所有人更繁忙。
沈勤提了几次后索性便不再开口,只对二老多说一句他忙,顾不上回家探望。
想到这里,沈勉禁不住嗤笑一声,看着两张慈祥的笑脸冷冷地想:回或不回,并没有什么区别,他早就看透,自己从没被真真正正地当作是“沈家人”。
充其量,不过是个在乡下养出一身坏毛病的野孩子罢了,抵不得他们聪明懂事的大儿子半分的优秀。
叁
沈勉对着二老的遗像观望了一会儿,将两张相框的距离调远了些,才觉得勉强顺眼,便扭头进了院子,绕着走了一圈,又对栽在卧室窗前的无花果树开始挑剔——树荫太大,透不进一丁点阳光,紧挨着无花果树的是棵过于茁壮的香樟,到了夏天就招惹出满树烦人的知了,使人不得安宁。
唯一的好处大约只有春天里树梢上摘几把香椿嫩芽,拌上鸡蛋翻炒,鲜嫩得与春天如出一辙。
他记得那种味道,是从前母亲常做——也许并不是常做,香椿芽只有短短一个月鲜嫩期,剩下的许多个月份,大家都是在对它的想念和期待中度过,成年后的沈勉再没有儿时的口福,三十年来,竟一口香椿炒蛋都没再吃过。
也不是没有机会——生意场上胡吃海喝惯了,他自诩见识过些场面,农家生态宴也吃过不少,独独对香椿炒蛋避讳莫深。
他从小就是个凡事都习惯向前看的人,成年之后更是忙得挤不出任何忆苦思甜的时间,对香椿炒蛋的寥寥几句评价,便是他对过往记忆的唯一追溯。
沈勉昂着头,眯着眼沐浴春日的阳光,透过冒出几簇嫩芽的树梢看向微蓝的天空,脑中紧绷多日的弦又松了些,仰着脖子对着鲜嫩的香椿芽走了一会儿神,才被隔壁的狗吠声拉回了思绪。
不如今晚就炒一盘香椿炒蛋,他突发奇想:正好能就着刚烙好的葱油饼和红豆粥,好好安慰下自己被烟酒折腾得脆弱不堪的胃——
可来回走了几步,忽然间又苦笑一声:自己大约被连日的变故冲昏了头,竟忘了魏燕那个忘恩负义的女人早在他出事的当晚就收拾行李跑没了影儿。
那女人烙得一手好饼,是在自家小小早餐店里练出的手艺,没跟着沈勉之前不过是个小小的服务员,在一水儿的老丑里有种鹤立鸡群的漂亮,笑起来一对儿小酒窝,看起来没心没肺。
他不免觉得有些可惜——若不是突然出了这样的变故,说不准他会娶了这个烙一手好饼的女人。
葱油饼,香椿炒蛋,红豆粥,三样缺了哪一样,都不能算作是一顿完满的晚饭,他索性不再去想香椿芽勾人的味道,一心一意地推开门,准备在里屋的卧室昏睡一场。
老屋许久不曾住人,哪怕是提前打扫了一通,仍然有股冷落的味道,天花板是极奢侈的高,孤零零地悬着两只朴素的灯泡,上头落了陈年的积灰。
沈勉年少时曾颤巍巍地爬上竹梯,扭着身子为它换上灯泡,沈勤在他身下仰头看着,两只手紧握着竹梯两端,与他极相似的眉眼紧张地蹙着,一只脚死死地把着竹梯。
他与沈勤是双胞胎,仅仅是探出头时晚了短短几分钟,两人的命运便天壤之别——沈勤如今已经爬到了副院长的位置,膝下一双儿女,个顶个的孝顺。
而沈勉落魄得只剩身上一套皱巴巴的西装,散发着隔夜的烟味,头发鸡窝似地支楞着,眼睑下方两块硕大的眼袋,形容狼狈到还不如天桥下的流浪老汉。
沈勉对着门边的等身镜打量自己几眼,抬起眼皮,望着正对着门的供桌,两副黑白色的照片并排放在正中间,前头放了些新鲜的水果,还有一尊精致的小香炉,处处透出被人时常关照的样子。
他对着两张修得有些失真的照片,终于忍不住情真意切地怨恨起照片上的人来。
肆
人之一生,不幸之事十之八九。这道理至沈勉如今的岁数,已经足以用亲身经历被验证。
可沈勉时常觉得,自己的不幸要比其他人来得更早,埋藏得更深,爆发得更加剧烈,以至于一爆发便将他半辈子的身家全都搭了进去。
所有事情都要向前追溯,一直追溯到四十几年前的某个普通的下午,三点,或许是四点,他在沈勤响亮的哭声中挣扎着出声,交错的哭声划破平静,随即而来的是惊喜的喊声。
这本该是个皆大欢喜的时刻,以至于沈勉找不出任何的借口去为他们辩护,究竟是做什么打算才干脆利落地将双胞胎中的他转手送到了乡下的远房亲戚手里,又究竟有什么样的盘算才又辗转将他接回了这个满目陌生的家中。
沈勉在乡下一直待到了十二岁——一个爹不疼娘不爱的尴尬年纪,在麦田里浪了一圈后顶着通红的脸回到家,便看见父亲——他名义上的养父,皱着眉头蹲在门槛上吸一支皱巴巴的烟,见他踏进屋内,便招手要他过去。
养母刚生了个白胖的小弟弟,“咿呀咿呀”地在里屋闹腾,沈勉怀里藏着一大捧狗尾巴草,心里惦记着去逗弟弟,却连里屋的门都没能进去。
来接他的人一身城里的派头,西装和连衣裙配得相得益彰,站在灰败的土屋里显得那样格格不入,女人唤他小名,声音甜腻腻的,叫沈勉听了有些不舒服。
他甚至还没能弄清来龙去脉,便被催促着收拾行李,拎着一只缝了好几块补丁的帆布包跟着这两个不速之客上了车。
记忆中的麦田绿油油的,散发出蓬勃的气息,倒映在视网膜中,潮水一般向后褪去。
他抱着包蜷缩在车后座上,身边是浑身上下透着教养的城里女人,沈勉察觉到她对自己的打量,甚至察觉到了那打量中暗藏着的不满:他的破了只洞的胶底鞋,脏兮兮的头发和沾了杂草的裤子都是那目光的对象。
沈勉压下一些隐约的惆怅,不得不再度缩紧了身子。
傍晚时分,沈勤的电话不期而至,沈勉刚刚从一场险象环生的梦境中惊醒,瞪着眼直直地望向天花板,直到被铃声打断。
“在家,”他揉了揉并没太大好转的太阳穴,觉得自己可能需要几片镇痛药,或者干脆再蒙起脑袋昏昏沉沉地睡上一觉。
然而沈勤并不打算给他这个机会:“晚上过来吃饭,你嫂子说要给你接风。”
沈勉被“接风”两个字刺得牙龈生疼,苦笑一声道:“哥,你就别挤兑我了,我这哪有脸说什么接风?”
说是逃命还差不多——成堆的订单都堆在厂里发不出去,几个客户都听到了风声,货退得比交定金时快了不知几倍,常用的号码已经被他关了机,手上这个还是临时办的新卡,用沈勤的身份证。
沈勤在电话那头沉默良久,终于道:“小勉,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有多少要还?”
回来的路上,沈勉大致和他透了底,幸亏出事时刚过了年,他手里几笔单子都收了回来,勉强糊住几笔大的赔付,厂也托人抵了出去,将大头给堵上,可还剩下几个小单子,凑在一起仍不是个小数目。
沈勉咂咂嘴,咂出了一丝苦味:“没剩多少,我头还有点疼,今晚就算了,明天罢。”
他不等沈勤再开口,便先一步挂断了电话。
伍
沈勉逃得过当晚,终究没能躲得过第三天,沈勤从医院回来便拐进了小巷,沈勉睡眼惺忪地给他开门,身上挂着衣柜里随手找来的睡衣,上头布满穷酸的褶皱。
沈勤打量他几眼,似乎松了口气,踏进门道:“怎么睡到这个时候?”
沈勉揉揉眼,哈欠连天:“还没休息过来。”其实他昨晚做了整宿的噩梦,梦里催债的声音如同一张紧密的大网,铺天盖地地砸下来,将他捆得险些窒息。
“你这样反而会扰乱生物钟——”沈勤的职业病浮上来,忍不住皱着眉就要说教,话到一半又住了口。
沈勉在心里冷笑:他明白,沈勤这是舒坦日子过得太久,对于沈勉今时今日的处境根本无法感同身受。
沈勤绕过他进了院,四下打量一眼:“你把缸给砸了?”
沈勉接了缸水漱口,含混不清道:“砸了,留在那招蚊子。”
沈勤不在意的笑笑:“你小时候最喜欢那缸了。”
沈勉一口水吐在青砖砌成的池子里,将水随意地一抹,没有接他的话茬。
但这依旧阻挡不了沈勤留在老院和他一起吃午饭的事实——他显然是有备而来,从后备箱里弄出一箱酒堆在餐桌旁,四样小菜摆得方方正正,大有与沈勉不醉不休的架势。
沈勉打量他一眼,心里无名的烦闷更多了些:沈勤向来是一杯倒的货色,儿时家里聚餐,被长辈哄着喝了一杯哈啤,便睡得不省人事,期间发了次酒疯,多亏沈勉在旁边盯着才没出什么乱子。
沈勉就不一样,他从小便被人用筷子沾着酒喂着长大,刚回家那年跟爸妈大吵一架,一个人偷了钱到大排档喝光了一瓶牛栏山,这些年来又在生意场上浮沉,十个沈勤也不是他的对手。
沈勤扬起下巴看他:“坐,我让你嫂子提前准备了菜,今儿就咱们哥俩。”
沈勉不情不愿地落座,背对着二老的遗像,总觉得背后飘着股冷意,桌上摆好了四个简单的小菜,看样子是自家做的:一道香椿炒蛋还冒着热气,花生米烹得有些老,小葱拌豆腐拌得七零八碎,看得沈勉胃口全无。
其他尚且不说,他心里想:单论自家女人做饭的手艺,沈勉是绝对远超沈勤一大截子的。
沈勤已把酒杯满上,先恭恭敬敬地奉了一杯给逝去的双亲,然后才重新落座,举杯看着对面与自己八分相似的兄弟:“这些年辛苦了。”
沈勉低着头只是沉默。
沈勤脸上的笑容敛了:“行了,别这副丧气样子,人只要没事,其他的都可以再挣。”
呵,说得倒是异常轻巧。
陆
酒过三巡,箱子空了一半,沈勉喝得偏,闷头便是一大杯,他喝酒生猛,是生意场上练出的速度,三满杯下肚,生意就要谈个八九不离十,趁着酒精麻痹大脑,半醉半醒间是最易煽风点火的关头。
沈勤并不吃他生意场上那一套,只是端着自己的一小杯酒慢悠悠地喝,看得沈勉心里急躁,索性自顾自地斟满,两人对面坐着,仿佛倒影一般。
沈勉趁着酒意仔细地打量自己这位旁人口中事业有成成熟稳妥的孪生哥哥,忍不住哼道:“咱俩还真长得不是一般的像。”
沈勤推了推眼镜:“同卵双胞胎,当然会像。”
沈勉又闷下一杯,任由酒精烧灼喉管,摇头道:“不像,其实咱俩一点都不像。”他猛地回头,笑着打量两张遗像:“你可比我幸运多了,要是当初抱走的是你——”
“怎样?”沈勤平静地反问。
沈勉觉得自己有些醉了,又觉得脑子里再没这样清醒:“咱们俩就不会是如今这样的境地。”
“你比我要有本事得多。”沈勤淡淡说道,听起来像是讽刺,偏偏说得极其认真,沈勉抬头打量他,想从他那副保养得当的脸皮里看出点东西来,却没能如愿。
沈勤接着道:“前两年妈还在的时候,常念叨你。”
沈勉眉头一跳,不动声色道:“念叨什么?”老太太走前两年脑子已经不太清楚,人和路都认不全了,无可奈何地被箍在家里,沈勉难得回去,被她攥了手唠叨个不停。
“说你有本事,长出息,是个做大事的料子。”沈勤想了下,抬手将酒斟满:“咱妈看人没错过。”
沈勉揉了揉脸,自嘲一声:“就我这副样子,算什么有本事。”
沈勤定定地看他:“做生意,哪有一直稳赚不赔的时候。”
沈勉只当他高高在上地摆着兄长的架势,只苦笑着闷头喝酒。
沈勤却没打算轻易放过:“说起来,这些年你变化可真不小,当初刚回来,跟个小皮猴似的,黑不溜秋往墙根一杵,一说话就脸红。”
沈勉也笑:“哪能跟你比,从小被咱爸妈捧手里,回趟乡下还把人家麦苗当韭菜给剜了。”
沈勤失笑:“你怎么还记得这档子挫事儿?”
这勉强算是沈勤顺风顺水的人生中一件小小的挫折,城里的孩子五谷不分,沈勉却是从小养在田头的,眼瞅着沈勤下了麦田就开始糟蹋,却抿着嘴不吭声,直到大人们赶到,揪起两人就是一顿狠训。
时间隔得太久,以至于沈勉压根记不清事情究竟是如何收场的,只晓得沈勤大约没发现他小小的心计,皱着眉头,手里还依依不舍地抓着一撮“韭菜”,老气横秋地安慰他,叫他不要害怕。
饶是沈勉对沈勤有再多的看不惯和不满意,也依旧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好孩子,长大之后也理所应当的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几十年来对待沈勉的桩桩件件也称得上是个好兄弟。
可要是当初被抱走的不是自己而是沈勤,或许摆在沈勉面前的,也会是这样事事顺风,样样顺利的人生。
柒
沈勤并未察觉到沈勉此刻内心的翻江倒海,他酒量不好,已经有了几分醉意,脚下开始虚浮,说话也不大清楚,沈勉也强不到哪去,只是硬撑着,不肯被酒精轻易控制头脑。
说不上是有意还是无心,这一对双胞胎仿佛阴阳两极,分割得彻彻底底。
沈勉少时就没半点稳重的样子,兴致勃勃地辍了学,放话要外出闯荡,而沈勤考上最好的大学,读研,又当了博士,毕业后顺理成章地进了中心医院,节节晋升,到如今势头才有所放缓。
沈勉还记得那年他博士毕业,自己特地赶回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远远地瞅见沈勤站在一堆人中间,是意气风发的模样,周围的几个女生长发飘飘气质非凡,他理了理身上的西装,硬是没敢凑上去。
后来经沈勤搭线,他还曾与其中的一位短暂地拍过拖,可惜人家到底是心高气傲的高材生,嫌弃沈勉一身铜臭味,没多久便好聚好散。
不是所有人都如沈勤一般,配得上安稳平和的好日子,他沈勉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在生意场翻云覆雨又如何,知天命的当口,还不是被当头一棒打散了他所有气力?
桌上的菜已经被解决大半,这是沈勉经历过的最难挨的一次酒局,沈勤脸上显出八分醉态,还晓得掏出电话叫人来接,打完便一动不动地坐在椅上,半阖着眼似睡非睡。
就连这点与沈勉也是截然不同:沈勉酒品难得一见的差,除去不动手打人,撒泼打滚样样占齐,以至于每年回家过节他都提前叮嘱自己酒到八分就收,不能被看了笑话。
客厅里瞬间安静了下来,沈勉红着一双眼,有些茫然地看了看四周,心中仓皇地奔出无助与凄惶,昨晚入睡前,他盯着空落落的天花板,心中竟萌出找根绳了结的念头。
只是天花板实在太空太高,沈勤又紧接着一个电话打来,彻底搅乱了他了结此生的荒唐想法。
沈勤没能在老屋打太久的瞌睡,沈勉的大嫂随即赶到,两个人架着他送进了车后座,沈勉晕晕乎乎地退回来,冲车窗招了招手,愣愣地目送着车尾消失在巷口,才恍惚地往回走去。
客厅里的饭菜没来得及收,空气中因此圈着几分烟火气,香椿炒蛋只剩了几粒零星的蛋碎,意外地受两兄弟的一致欢迎,沈勉打着火,烟却捏在手里,半晌也没能点燃。
而桌子对面的老式红木椅上,烟灰色的毛线坐垫的一角,静静地躺着一张卡片,和一张稿纸用细橡皮筋捆在了一起。
沈勉眯起眼瞧了好半天,才越过桌子将卡拿在手里,稿纸抽出来,上头简单写了六位数字,沈勉依稀记得是二老的忌日。
他下意识地将卡摔在桌子上:“妈的!”
没人能理解他突如其来的怒气,包括沈勉自己,他觉得自己被人兜头扇了一巴掌,火辣辣的疼带着耻辱感瞬间将他淹没。
捌
沈勉如同困兽般,在房间里焦躁地踱来踱去,卡仍旧扔在桌上,沈勉尽力让自己不朝它望去。
或许是酒精作用,沈勉觉得胸膛一阵一阵地涌出难言的火气,掺杂着暧昧不清的其他情绪,叫他更加的心浮气躁。
他来回晃了两圈,突然被客厅的一角吸引了注意力,角落里的小茶几上零落地摆了几只杯子,杯子后的墙上倚着一个老旧相框,里头是一张全家福,被保存的看不出一点儿时光的痕迹。
沈勉神使鬼差地走了过去,眯了眯眼,将视线定在上面,被酒精麻痹大半的大脑慢腾腾地反应过来,这是初二那年全家在照相馆里的合影。
那时沈勉已经开始长个儿,初来时对自己身高的惶恐在膝盖的疼痛中得到了缓解,发育期截止前,他甚至比沈勤都微微高了个头顶。
照片里两人的身高已经持平,沈勉站在正中间,左右手挽着中年夫妻,沈勤和弟弟妹妹站在后头,六个人脸上是如出一辙的欢喜。
沈勉却对这欢喜毫无印象,或许是人的记忆太过趋利避害,只记得划在心口的刀伤,却总是轻易放过化在水里的方糖。
沈勉对着照片观望良久,依旧没能在稚嫩的少年脸上找出灰暗的痕迹,反倒牵扯出不少经年的往事,鸡毛蒜皮般一窝蜂被追忆的风吹了出来,糊在脸上,使他一颗干瘪的如缺水海绵的心,一不留神便跌入了往日的海洋里,迅速地膨胀。
他想起许多年前的一碗槐花饭,就着蒜泥大快朵颐的满足感,香椿叶的清香扑鼻,趁着金黄色的蛋液,下锅翻炒出一盘春日的新鲜,葡萄藤上刚刚抽出弯曲的细丝,石榴树花开的艳俗又招摇。
而他躲在院子的一角,趴在那口沉重的石缸前,望着波澜不惊的水面,经年的雨水沉淀出一层又一层沉郁的绿色,上头倒映着他郁郁寡欢的脸。
忽然间水面被击的支离破碎,沈勤大汗淋漓地朝他跑来,将沾了水的球抱在怀里冲他招手,篮球富有节奏的撞击着青砖,沈勉转过头,看到中年女人隔着窗户笑吟吟地望过来。
后来这些场景慢慢地褪去了,如同那年乡下涌动的麦田一般,只留下几个模糊的片段,少年的他颤巍巍地扶着竹梯,伸长了手去勾悬在半空中烧断了钨丝的灯泡,小腿止不住痉挛。
沈勉在午后尚且灿烂的阳光下,神色莫测地枯坐许久,终于攥紧了手中的卡,一如几十年前的那个午后,双腿打颤的少年攥紧了手中稳固的竹梯。
沈勤就站在竹梯下,双脚把着梯子两端,扬起一张与酷似自己的脸,盯着他冲他笑了笑,手臂微微用力,竭力将摇摇晃晃的竹梯贴在墙上保持平衡。
他说:不要怕,
有我在。
作者:温难(微博:@温难酱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