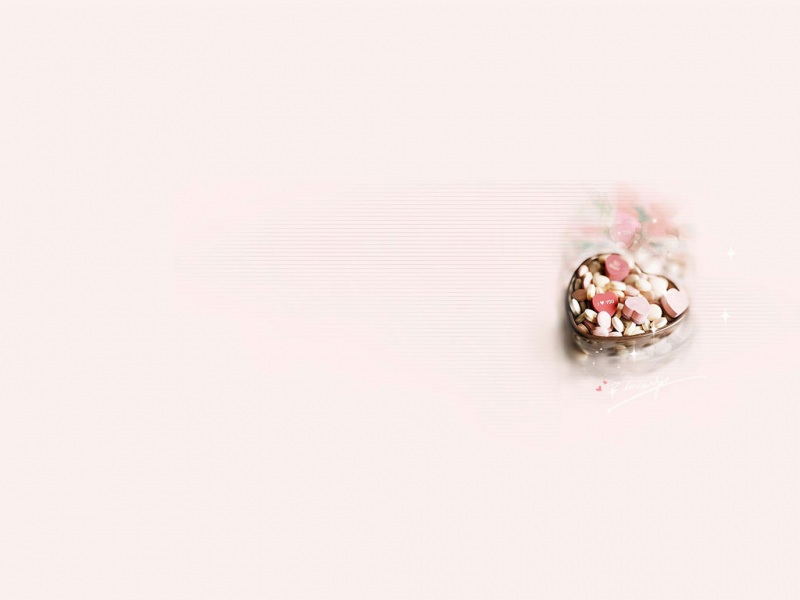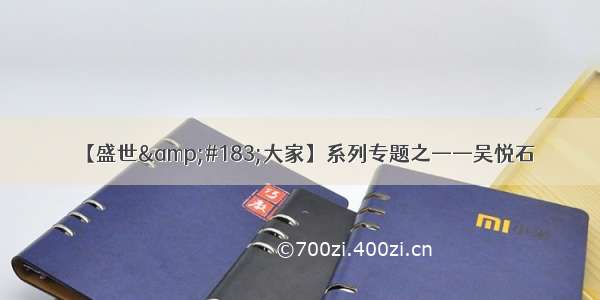
中国书法网【盛世·大家】系列专题
吴悦石国画展
吴悦石
1945年生,现居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院艺委会主任,中国国史研究编修馆研究馆员,中国国家画院吴悦石工作室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中国画学会理事,北京水墨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元社顾问。出版有《吴悦石画集》《吴悦石作品集》等。
大处落墨 气势撼人
——吴悦石先生当代大写意中国画读后
徐贤/文
我读吴悦石先生的作品很多,真人却只见过两次。
给我的感觉吴先生是一个矛盾体。看他的画,不衫不履,大处落墨,气势撼人,真有“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之势,还以为是个关西大汉,手持铁板铜琶,高唱“大江东去”,及见其人,竟恂恂然儒者风范。
吴先生的画取材佛教故事很多——罗汉、达摩,还有他常画的钟馗,他也自称三宝弟子,是正规受戒的居士,法名“道成”,但他的艺术实践和主张却常流露出儒家的入世与担当。他六十多岁了,还能牺牲很多宝贵的创作时间,应国家画院之邀开一个导师工作室,带十几位弟子,努力带领当代大写意中国画走出“式微”的态势,这份雄心壮志似更贴近儒家。他主张大写意画家要具备足够的经学修养,这更是儒家“今文经学”的范畴了。而“即心是佛”的修养使他的画时常流露出禅的空灵。比如《荣宝斋画谱·吴悦石卷》中有一幅《松坪禅对》,一位老僧恬然入定,一小僧侍坐于侧,一小僮兀自煮茶,两老松苍翠古茂,联想到宋徽宗的《听琴图》,都是让人产生无限遐思的画,看徽宗的《听琴图》,我们也能从悠扬的琴声里读到清远的宋朝,但吴先生此作的境界似乎更加幽远虚空。
一个画家光有深厚的学养功夫没有过关的技法,或技法娴熟学养不足,是有可能成为名家却不能成为大家的。吴先生恰恰是技法全面学养又深厚,所以他成为大家是必然的。
吴先生早年于宋元下过很深的功夫,现在画山水依然可以很工细,他的花鸟画能于吴、齐之后立此一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文心雕龙》说:“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鍠。”吴先生的花鸟画,写来真的是云霞雕色、草木贲华,林籁结响、泉石激韵,尽管依然承袭吴、齐红花墨叶的画法,但即使是不常看画的人,也会觉得他画得很自然,不造作,似乎自然界的花花草草本来就是红花墨叶,这也许是中国画生命力的所在吧。
吴先生的工笔草虫、鞍马更是丝丝精到,笔笔传神,他的人物画无论是细勾的罗汉像还是逸笔草草的钟馗,都画出了他的个人面目,乍看线条、笔墨依然不出吴、齐家法,细看之下,吴、齐又无此面貌。吴昌硕人物画罕见,王一亭的钟馗不是此貌,齐白石的也不同。可能是吴先生自幼学习形意拳的缘故,他笔下的人物姿态随意,从不装腔作势,却都很舒服,精气神十足,似乎是得益于形意的修习。闻说当年京剧大师余叔岩教李少春《战太平》,花云有一个亮相,李少春总演不好,自己也觉得别扭,余叔岩并不示范,只告诉说“什么时候你自己觉得舒服了就对了。”“自己觉得舒服了就对了”其实是更深层次的艺术规律。吴先生积数十年学拳之功和临池之力,加之人生阅历之积累,自是出手不凡,看他画画很舒服(我只在网上看过视频),他笔下的人物也都很怡然,这样的画别人看了也会觉得舒服,这就是自娱娱人之乐了。有些画家把钟馗画得金刚怒目,这样小鬼肯定会害怕,但恐怕这样的画挂在家里,孩子晚上看了也会害怕。吴先生的钟馗不同,很威武,又很和善,很粗豪,却仍不失“终南山进士”风范。近代学者黄季纲先生主张“学问文章,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以高明广大为贵。”吴先生的艺术主张似与此契合,他画钟馗,旨在为民祈福迎祥,他主张要画光明的东西,画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堂而皇之地欣赏的东西,时下有些画家画很私密的东西,吴先生却不主张如此,是故他的画作,哪怕是不足一平方尺的小品,皆有大气象,是正大光明之相也。当下风水之学大兴,吴先生的钟馗,特别是朱砂画的钟馗竟成众家追捧的对象,似乎渐成家庭陈设之时尚。财力盛者买一大幅,财力弱者买一小幅。但先生的画这几年涨得比楼盘还快,已不是寻常百姓所能够问津了,于是退而求其次,吴先生画作的复制品竟也大有市场。前些年一张《福从天降》的复制品做了一万张,由先生的画友会分赠诸友,结果备受欢迎,一时洛阳纸贵。吴先生之花鸟画,如书之王羲之,京剧之谭鑫培,大鼓之骆玉笙,得中和之美;吴先生之人物画,如书之颜真卿,京剧之杨宝森,大鼓之侯月秋,得雄浑之致。然雄浑之致易得,中和之美难求,时下京剧十生九杨,良有以也。日后坊间钟进士像能否十钟九吴样或尽作吴家样抑未可知。
许氏《说文》:“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左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何也?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衍误。是以绘画一道历来重视口耳相传。吴先生以半世之功,古稀之年,大开山门,广纳弟子,耳提面命,以期吴、齐一脉大兴,中国大写意不衰,中国文化之脉不绝,是真儒者之担当,是真释者之愿力,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与先生这种博大襟怀和抱负相比,先生的画似乎又可以退居为其传经布道的手段和载体了,然而就是这手段和载体,也足以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光辉的一瞬了。
纯正的中国画味
——吴悦石人物画品读
许华新/文
说起中国画味,人们就会回忆起历代的中国画作品,它们所传达出来的整体形象,在每个读者心中都形成一把尺子,使其得以对林林总总的中国绘画形成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中国绘画,自其始创之时,就不像西方绘画那样追求对自然物象做科学而忠实的描绘,而更注重传神写照,以求作者意趣、心性与自然的高度融合。早在魏晋六朝,顾恺之就提出了“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等理论,再到宗炳的“以形媚道”,谢赫的“气韵生动”,直至元代倪瓒的“聊写胸中逸趣”和清代石涛的“吾与山川神遇而迹化”等,历代画家都在绘画中实践着“天人合一”、“物我合一”和“技道合一”的审美理想,逐渐形成典型的中国画的审美、品评标准,特别是在宋、元以来形成的文人画传统逐渐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审美意识,在这种审美意识下所形成的绘画风格,整体上也呈现出典型的中国画味。顺沿着这种传统,历代都有一些有责任感的画家以自己的绘画实践、探索着传统中国画的延续与发展,细心维系着纯正的中国画味,当代画家吴悦石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传薪者,他正以自己的绘画实践探索着中国画在当代语境中的传承与发展。
读吴悦石先生的人物画,很难逃脱其画面弥漫着的文人情怀的感染。观其画面,无论是匠心独运的位置经营,传神的人物写照,简约的人物造型,随性而发的书写性笔墨,富于文化内涵的题材选择,还是富有深意的题画诗文和意味无穷的书法,都在经意不经意之间,传达着浓厚的文人气息,这般境界,非深厚的文化积淀不能企及。
观吴悦石的人物画造型,我的第一感叹是其为真懂画者。出此论断主要基于两个依据:一是其深谙传统人物画简约、传神的造型规律;二是其精熟中国画的笔墨造型理法。对于前者,二十世纪以来的西学东渐,西方学院派美术教育模式对现、当代中国人物画的造型方法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徐悲鸿为代表的用西画方法改良中国画的思潮一直左右着当代中国画的教学与创作方向,这种改良在推动中国画变革与发展的同时,也削弱了中国画自身的特色,也就是削弱了中国画原有的味道。体现在人物画造型上,当代许多画家忽略了笔墨和线条的造型锤炼,而用皴擦等方法在画面上表现素描效果,并一味地抠颧骨和人体结构,导致画面徒有其形而精神、趣味全失。针对这种弊端,潘天寿早就告诫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的学生说:“把注意力放在颧骨上很难画好中国人物画。”吴悦石深知此理,其延续正统的中国画文脉,继承顾恺之、吴道子等人的传神写照方法,承接梁楷、陈洪绶和齐白石等简约而富有意味的造型手段,以便追求个人理想和人物画造型的高度统一。品读吴悦石的人物画作品,往往被其所塑造的人物精神气度所打动。无论是抚琴的老者、扫地的顽童还是目送归鸿的高僧,作者都赋予其启人心智的造型意味,传达出准确的精神情态,寥寥数笔,甚至仅人物的一个背影,就能传递饱满的情感和精神,足见作者的意象造型功力。中国画家虽众,而能精通中国画笔墨造型规律的却寥若晨星。许多画家认为中国画主要为线条造型,殊不知线条并非中国画所独有,诸如米开朗基罗、安格尔、毕加索、马蒂斯、米罗、克利等,许多西方绘画大师都是玩线条的高手,而笔墨造型方为中国画造型的精髓所在。通过笔墨造型不仅提高线条的质量并使其变化无穷,更重要的是笔迹墨气的运动变化体现着作者生命节奏的律动和宇宙运动的气机,是作者通过绘画达到“天人合一”的重要途径。故古之论者有云:“俗人喜画之寓意形色,雅士赏画之笔墨气度。”可见,能解笔墨气度的画家,画格一定不俗,而吴悦石正是深谙笔墨气度的画家。
吴悦石人物画的用笔,可谓既狠又准。观其作画,每每先相纸多时,使意象孕育于胸,每一下笔,则如同野战,笔笔写来,气机通畅,腕随于心,笔从于腕,千变万化,出于天然。此番忘我之状态,使其用笔全由意出,时而沉着痛快,时而举重若轻,变化万千,笔所到处,心迹藏于其中,笔未到处,意趣亦含其间。更为可贵者,随意书写之笔线,既能准确而简练地刻画出人物造型,又能微妙地传达人物的精神气度,可谓“形神兼备”也,此种境界,非经千锤百炼不能达到。黄山谷云:“心能转腕,腕能转笔,书字便如人意。”宾虹论用笔曰:“当知如金之重而取其柔,如铁之重而取其秀,金之重,而以柔见珍,铁之重,而以秀为贵,米元晖力能扛鼎,重也,而倪云林之如不着纸,亦未为轻。”用笔如不着纸,飘飘有神仙之气,不谓不重,而是举重若轻。吴悦石先生之用笔能如此轻重自如,收放随心,尽用笔之能事,深得用笔三昧。其用墨则或焦或淡,皆能给人苍润之感,深含古意。
在画面的位置经营上也体现了吴悦石先生过人的智慧。其笔笔生发,一气呵成的作画方法已使画面气机连绵不断,形象开合有致,顾盼通情,生动感人。而极少的笔墨语言,简约的造型元素,经由画家以诗书画印综合呈现的形式巧妙地结合到画面里,在大开大合的画面构成中不露痕迹地体现着相反相成的造型规律,同时传递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和真切的文人情怀,让人感染于其所营造的精神氛围而忘却其经营所在,此乃万法于胸,殚精竭虑,又终归乎天然。
中国画的品评历来以人品决定画品,这里的人品主要指人的整体文化修养。吴悦石先生早年得到画坛耆宿的亲授,又为国画名家王铸九、董寿平的入室弟子,积累了丰厚的传统文化根基,这些都为其绘画题材的选择、诗书画印的综合呈现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持,也是其人物画能保持纯正中国味的基础,加上其一贯坚持的文人画创作道路,逐渐成就其高迈旷达的绘画品格。宋代书画家米芾认为书画作品的功能主要是供认雅玩清赏,令人精神愉快。今观吴悦石先生作画,痛快;欣赏其人物画作品,在愉悦中还得到启迪。深厚文化修养,平淡旷达的个人心性,使吴悦石身则诗人,犹有仙骨,如山林之僧,枯淡之外,不作它求。加上其纯正、精深的笔墨语言,使其人物画能出尘格,含新意,形成天真、平淡而又奇绝的画格,成为标立于当代人物画坛的一枝奇葩。
水澄镜朗 花月宛然
——读吴悦石绘画
汪为新/文
十几年前,甚至更早些时候,吴悦石先生便已名满京城,当人们对他的才情、胆略及日后发展气象颇有期待时,他却突然消声匿迹,蛰伏海外十数年,音信杳无。所谓“疏纵不为儒缚”,是“英雄失路”还是“独立一时”?人们的常规性预言往往是按照世俗的一般规则去推断某个人的行为轨迹,而智者却时时能超出常人之想。多少年后重新见到悦石先生,他依然躬耕不缀,且率性而行,比起早年的才情锋芒来,似乎多了几分淳厚与积淀。
中国写意绘画以素纸为底,以宏观世界或微观世界为描述对象。但以“象”达意,似乎还远远不够,因此素养与人格魅力、气格与精神情怀被置于崇高地位。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悦石先生为人有安世侠烈之气,磊磊落落,画格自然绝不从俗沉浮。外表温文尔雅,内心桀骜不逊,对于那些狂肆其外、枯索其中的为人或为艺甚为不屑。
这种处世态度也体现在他的作品中:挟风霜而走雷电,或高山流水,或老者静观,或野渡浮筏,或空鸟掠飞。有雄浑如大海之奔涌者,老健如朔漠横雕者,明净如乱山积雪者,高远如长空片云者,或“意”或“象”,一一具已。
历代作品里不管是夏圭的“苍洁高迥”,抑或倪云林的“天际渺长苍”,都不足以遮蔽艺术家得其意而境出。“得意忘象”便成了艺术家倾注热情的最好托词。
“得意忘象”源于《庄子·外物》之“得意而忘言”,魏晋时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引申为“得意在忘象”,宋黄伯思曰:“昔人深于画者,得意忘言。”对于写意花鸟来说,此意似乎更为明了,历代花鸟画大家也大都“略起玄黄,取其驵隽”,尤其是明以后,花鸟画把“意”推到极致,连徐悲鸿都说:“造诣确为古今世界第一位者,首推花鸟。”在悦石先生涉猎的艺术领域,窃以为他的花鸟作品最能体现其酣畅淋漓的艺术追求,那种愤激之情发诸毫楮的壮士气概,似乎比起他的人物和山水来得更加融浑一体,一管秃笔犹如挥毫列阵,统帅画面若壮士横刀,大处着眼,小处着笔,气高时如行空之天马,从造型到造“意”,有“一扫白电愁长空”的慷慨激昂,呼号奔走中豪迈之气激射而出,画家笔下的葡萄、芭蕉、松树,好一派“粗布乱服”的景象,待掩卷后又觉得淋漓中初闻雷电过后短暂的恬适,翻开则又回到精神灿烂,如是反复,才猛然感受到他的才情。
当然他更像是一位艺术家而非画家,因为他那半隐的生活方式和闲云野鹤般的情怀决定了他放逸不拘的创作态度,故题材上不管是花鸟还是人物山水,工具上不论是毛笔还是手指,得于心,应于手,皆触类而旁通。从悦石先生学艺途径来看,他早期作品有很多人的影子,甚至也有许多当时风行的对大河大山的歌功颂德式面貌,但那种流于形式表面的东西很快被扬弃,因为除了对传统的认知外,强劲的学养支撑是悦石先生得以刀枪不入的根本保障,取而代之的是朗朗正气与磅礴的情怀。我从他画集的自序中知道,悦石先生是“少年学画”,并有“壮游天下”之履历,这与他近年的栖居京城寓所“静养”不无关联,他的确和许多艺术家一样,下过苦功夫学古人学近人,而关键的是他有自我的辨别、鉴赏能力,包括他个人的判断经验、稳健的心理和感情上的专注形成了自已独立的结构,从而在传达视觉张力的瞬间变得坚强。
在当下的文化背景里,如果说谁超出了世俗尘寰一切牵扰是大不然,我想也没有谁愿意成为天底下的孤儿,去苦守漫漫长夜。悦石先生也不例外,他笔下的芦汀茅舍、孤人独鸟只是外在事物灵魂的十足描写,而隐逸于作品背后的出世或入世观念则被作者的个人人格消融得无影无踪,但从中我们能看到一个艺术家如何地不屑于虚名浮利和患得患失。
从悦石先生的个人经历来说,很多人难以望其项背。他识广学厚,对玉器、木器等古董的鉴定,对历代绘画作品的精研使他得天独厚又触类旁通,“壮游”的经历又使得他心胸旷达。即使在文革中怀着“托足无门之悲”,仍无放弃之念,而在当下浮声浪气的繁华背后,悦石先生虽居京城闹市,但终日净几明窗,读书玩古,游于笔砚,他是否仍抱着儒家“退则独善其身”的情怀尚不得知,然而他对艺术倾注的极大热忱是宝贵的。诚然,这与传统文人隐逸山林或那种“济世终无术,谋生也欠缘“的被动归隐心态也是有天壤之别的。在当下繁华簇拥、物力充盈的盛世景象中,仍有静养心情去咏唱身边的粉蝶黄花,悦石先生的一切努力值得我们去深思。
兴酣落笔摇五岳
——吴悦石先生山水画蠡议
杜志宇/文
吴悦石先生以全面的国学素养和精湛的绘画技艺,已然成为传统文人画在当代的重镇。在传统文化式微的艺术生态下,先生卓尔出群的艺术风格和创作实绩显然成为一面飘扬的旗帜,流风所及,泽被青年才俊多矣,堪称文人画艺术作为本土文化的精髓终究还有着不朽生命力、尚有开拓光大之广阔空间的明证了。作为一种艺术现象,其个案价值和史学美学意义都是值得珍视并加以索隐探微的。
在吴悦石先生的艺术世界中,其花鸟画和人物画的成就已为大家所熟知,并得到专业人士的一致首肯,很多论者站在美学和绘画史以及艺术学的高度给予颇为中的的极高评价。其实先生山水画的造诣也是秀出凡俗、卓然独树的!实际上,先生从艺五十多年来,山水画也是其潜心以求的一个方面,将山水画作为精神家园和情感的归宿,以“适意”、“畅神”、“澄怀观道”为旨归,所以就文化含量和美学意韵来讲,在观念的表达、情感的抒发、笔墨语言的锤炼探索、图式的创造等方面,其戛然独造处是不在其花鸟人物画之下的。
“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众所周知,山水画流衍千余年,以中国特有的哲学思维和观察方法诠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文人山水画的传统,追溯起来,是从唐代王维的南宗画派滥觞,到后来的张璪、荆、关、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元四家等,都是以水墨渲染为尚,不讲究细腻入微的刻画写照,以气韵高雅为审美追求,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将山水画的社会功能变为了如诗文那样表达观念的艺术,彰显了文人艺术思想的深邃和意涵的丰厚,所以,宋代邓椿说的“画者,文之极也”,应该说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一发展脉络到清代“五僧”和虚谷等得以发扬光大,及至晚近时期,黄宾虹、齐白石等大师达到了颉颃古人的高度。黄宾虹以多元而深湛的艺术修养开拓了一个“浑厚华滋”的美境,以书法的笔意和积墨法的运用,集水墨内美之大成;齐白石则以不同时流的简洁明快取胜,画风简练概括,清新恬淡,一派质朴的田园气息,突出了艺术符号的象征性和概括性。因了山水画年代的久远和风格的多样,历代大家如高峰林立,对于当代山水画家来说,出新是个很大的难题。吴悦石先生的山水画转益多师,广纳博收,法资多方,在浑朴空 灵和潇洒酣畅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形成了抒情性、金石味特别强烈的艺术语言系统,突破了传统的套路而化合出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面貌。
吴悦石先生艺术发蒙于齐白石的入室弟子王铸九先生,得齐派艺术的真传,以书法、金石入画,凸显笔墨的情感表达和趣味经营,有非常坚实的笔墨基础,而山水画则以另一位老师董寿平先生的影响为大。造诣全面的董寿平先生山水脍炙人口,境象空蟹而深邃,画卷不拘峰石之形似,而求整幅气韵的统一,完美地代表着文人画那种天人合一的真髓,不仅具有诗画相兼的天然意境,还富有一种谦和醇厚的文人书卷气质和儒士风范。吴悦石先生在山水画诗意的营造和书卷气质方面深得乃师神髓,同时汲取了齐白石山水画以少总多、以简寓繁的特点,又兼揉石涛、石溪、黄宾虹鲜活的笔墨语汇,而笔恣情纵,不拘成法,又依稀可见八大山人的痕迹。在驰神运思、挥毫濡墨的创作环节,则不以袭用前贤的成法为能事,属于善学而能化者。因此我们读先生的山水画,往往感受到一种元气淋漓的质朴华滋之美,既有一种鼓荡生风的磅礴气象,又有耐得住咀嚼流连的诗性意味。在一件尺幅小品中,画两峰对峙,近处高岩上古松蟠曲,中间烟云飘荡,远处山峰烟树迷蒙,让人联想起“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的名句。笔墨运用舍弃了前人程式化的技法,突出笔墨的概括性和表现力,而以极为简明肯定、浓淡焦润变幻的线条写出大致的轮廓,辅之以墨色的渲染,略加皴擦,泼墨和点染都极富神采,虚实关系的处理大胆而新奇。所以令人目眩神迷,可谓尺幅千里。就在这幅画上,吴悦石先生题到:“山川形胜,不在眼中,只在胸中,试想朝晖夕阴、云卷云舒,如何写之?”这应该说也是先生对山水画的一种理解,即不必穷形尽态地模山范水,要在写出胸中之山水,抒发胸中之逸气,而以对自然的体察和悟对,用简括凝练的笔墨撷其一角完全可以达到涤除玄览、澡雪精神之效果,令读者“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想象到大自然朝晖夕阴之万千气象,而画家的胸襟气度一寓于中。正如石涛所说的“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画家在与自然的精神往来和情感交流中的独到体验,形诸纸面,而纸面上的境象绝不是对自然简单摹写和复制,而赋予它人文精神,获取物象的真气和神采,强化对自然的主观感知,具象的层面退居其次,突出“自我”。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一段论述:“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先生的山水正是在这一点上,在“写”与“造”之间突出“造”,着力表现经验的世界,所以有景、有格、有情、有韵,情境相生,情境交融,而因此也更熨帖地切中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脉搏。
见情见性的大写意画往往是小幅易作、大幅难图。不过吴悦石先生也擅作高堂巨幛,一如其小品画,以气胜而非斤斤于技,以神胜而非以形胜。《妙峰山晨曦》是一件六尺巨构,山势连绵,远处辽阔江天上,一抹晨曦中群山万壑隐然可见,构图奇崛,虚实得宜,笔墨圆活洒脱而见通透秀润,谱写出激越雄浑的旋律,透溢出画家对自然和生活的强烈热爱之情。另一幅丈二作品《蜀山印象》,视野开阔而境界博大,绝似“词源倒倾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有一种吞吐万象、囊括八荒的气概,展现了蜀地山水“飞湍瀑流争喧傎”、“高江急峡雷霆斗”的雄奇壮美,摄魂夺魄,观者不能不为之动容。此等境地,非大手笔无以写之,盖才薄怯弱者不敢为,功力不逮者无以为,学养不厚者不能为。
吴悦石先生的山水,突出的特点是线条的恣肆纵横、遒劲有力,墨象的变幻莫测、象外生趣,都以传统文化的底蕴和书法的书写性笔意为根基。艺术语言高度概括,笔简意足非斤斤细谨,有振迅天真充溢画面的夺人气势,足称对文人大写意艺术新天地的开拓。溯其所由,当是以青藤、八大等为代表的大写意艺术精神,沿波讨源,一超直入。而先生画面上特有的雅正浪漫气息、苍茫涩重的金石趣味、阅尽沧桑的深沉感、耐人咀嚼的视觉张力,则非笔者这篇小文所能尽述了。
末了,凑成拙句赞曰:“十年去国心犹壮,艺道胸襟两大成。兴酣落笔摇五岳,沧桑满卷意崚嶒。”
在无路处行走
——从吴悦石先生花鸟画创作想到的
韩少玄/文
一直感动于、也沉思着这样一则典故:阮籍常漫无目的地驾车载酒而行,待到再无路可行时,便仰天嚎啕。我能够体味他彼时凄绝悲凉的心境——路已尽,绝境横亘,究竟如何是好?此种境域,确乎是够难为人的。不过应该知道,真正意义上的哲思,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其实,无路可行作为一种普遍的可能性,我们随时随处都有可能与之不期而遇。艺术创作亦然。在上个世纪,文人画遭遇的是进退维谷的境地,文人阶层的消失、传统文化的衰退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变更等等,文人画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从根本上被颠覆了。所以,无论承认与否,当年李小山提出的“穷途末路”说,不过是阐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而已。
问题是,面对这一事实,在路的尽头,我们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在一种价值被毁灭后如何才能在残墟上重塑一种价值?因为,如果价值不存在的话,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将无法进行。可以看到,彼时的创作者,决绝的背弃文人画者有之,意欲“新瓶装老酒”或“旧瓶装新酒”者有之,而不多见的,是如吴悦石先生这样纯粹的文人画的坚守者。或许有人会怀疑他坚守的价值,或许也会有人斥之为顽固不化,但我知道,这样的论断是不确切的。吴悦石先生曾于海外生活多年,很难说不是异域的宗教信仰教会了他坚守。坚守,是在完全的黑暗、绝境中的希望,而信仰也只有在这一时刻才称得上是信仰。也许有人问,即便是存在延续了,会不会只是苟延残喘?如果是,那这样的延续又有多少意义?其实,对于缺乏信仰的者,他们是不会理解吴悦石先生的坚守的,而我,也是无话可说的。吴悦石先生于文人画的坚守,其意义只在于表征着在没有希望的时候只有不问目的、不问结果地坚持希望——即在没有路的地方走下去——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种选择,于人生、于艺术,都具有方法论的价值。而这,也就是我所认为的吴悦石先生绘画艺术创作的根本价值所在。
禅家道:那边会了、却须来这边行脚。——斯言甚是。
认识到吴悦石先生绘画创作的根本价值所在,自然是重要的,但也是不够的,还需要将抽象而概括的认识进一步落实到某种具体的实在,比如他的花鸟画创作,如是,才足以保证我在这里所谈论的不至流于空泛的想象,并且,我的判断的确也是来源于对其某些创作细节的观照。需要在这里申明的是,我之所以固执地眷顾着他的花鸟画创作,也只是因为我欣赏的偏好而已。
从整个绘画史的角度来看,吴悦石先生的花鸟画创作很明显地体现出对一种历史逻辑延续的必然性的倾心与向往。具体而言,吴悦石先生的花鸟画创作,似从清末以吴昌硕为代表的海上画派以及稍后的齐白石一脉延续而来,观其语言风格,这一点是不难确定的。而我所关心并努力尝试回答的,则是他为什么会着意于此,相信这绝不会是无意识的偶合。大约,吴悦石之所以选择吴昌硕、齐白石以资取法,其用意无外乎重续文脉。中国绘画的发展,从汉唐两宋以至元明清诸朝,其间虽有变易,文脉是不曾隔断的,当然这与几千年中国文化绵绵不绝的特性大有关联。遗憾的是,因着种种内部外部的缘由,这种延续性在上世纪却被生硬而野蛮地切断了。由是,中国绘画也就不无遗憾地或者拐入异途或者茫茫然不知所措了。不过,另觅新途也罢,茫然无措也罢,归根到底,文人画的命运注定被强行地扭转了。如果说,文脉的断裂或扭转源自其内部的逻辑必然性,倒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知道,导致这一切的,更多是来自外部的因素。那么,吴悦石也就有理由怀疑舍弃文人画固有文脉而另投他处的合理性,同时也就有理由在有太多的创作者津津有味地创造他们的中西合璧的绘画时,回转到吴昌硕、齐白石,回到文脉断裂的边缘。正因为不相信文人画命该如是,也因为认识到文脉断裂的偶然性,吴悦石的花鸟画创作以及他整个的书画艺术创作,就自觉地担当了恢复文人画在当下存在的重任。诚然,传统文人画所依赖的种种社会文化基础已然单薄,但是作为一种绘画创作的方式或形态,难道就绝对没有存在于新环境的独立能力?在路被外力堵死之后难道就不能继续前行?这是吴悦石先生所不愿意相信的。
自吴昌硕、齐白石一脉而来的吴悦石花鸟画创作,除却体现着其重续文脉的愿望外,在某些具体的创作手法上,也不可避免地受他们的影响。与吴昌硕、齐白石一样,吴悦石先生的花鸟画创作具有极其明显的以线造型的意识。一方面,书画同源、援书入画历来是文人画创作的显著特征之一,而尤以花鸟画为甚,吴昌硕、齐白石作为文人画的后期代表人物在这方面自然不会有所忽视;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吴悦石先生长于书法创作,也就为他在花鸟画中着意于以线造型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不过我想,问题不会这样简单。因为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除了被动的接受,恐怕很难见出吴悦石先生主动性的选择。与传统文人画创作不同的是,上世纪以来很多致力于中国画创作的现代性创新探索的创作者,他们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都倾向于块面造型的手法。以线造型和以面造型,尽管表面看来不过是手法的不同,但从更深层次而言,却表征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时空观念以及蕴藏于其中的文化哲学思想。不确切地说,中国的文化哲学精神讲究的是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特别在意历时性时间的绵延,表现在艺术创作中,即中国书法、文人画的“线”的运用;而西方的文化哲学传统,尤其是现当代以来,注重的是将历时性时间秩序打乱之后的重构,所以表现在艺术创作中则不免会倾向于块面结构的运用。在两相比较中不难看出,吴悦石先生在他的花鸟画创作中所运用的“以线造型”的手法,绝不仅仅是“为艺术而艺术”。通过线的运用,他是想把自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体悟融于其中,并且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对西方文化哲学思想的不信任,或者说,即便不拒绝向其借鉴、学习,其态度也是极其审慎的。似乎不难看出,吴悦石先生于此处的用心同他重续文人画血脉的意愿是一脉相承的。
再从文化属性以及审美意味来考察,吴悦石先生的花鸟画创作同样与吴昌硕、齐白石的绘画艺术相一致,即体现了对民众世俗情感的尊重。首先,吴悦石先生花鸟画中的世俗意味,是与宋元文人绘画中高逸、超脱、不染尘俗的品格相区别的。或许是因为明清以来市民文化的兴起及以绘画谋生的职业画家的出现,致使创作者失去了宋元尤其是元代文人的清高意趣,而世俗意味在文人画中的体现,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文人画作为一种绘画形态在内在逻辑上的悄然转变;其次,吴悦石先生花鸟画创作中所透露出来的世俗的意味,与当下不少学人所阐述倡导的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也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具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在,明清以来绘画中的世俗意味,其指向的接受群体是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区别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世俗民众,而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接受者却是现代化工业、商业兴起之后以消费为存在特征的群体,在文化属性上前者隶属于历史悠久的传统农业文明而后者则分明是后起的现代化工业文明的产物,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吴悦石先生在自己的花鸟画创作中所流露的世俗意味,如对牡丹、石榴、寿桃等等别具吉祥富贵民俗内涵的题材的选择,其实也表明他是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日益商业化、现代化的社会的思索与忧虑。甚至也可以认为,吴悦石先生在自己艺术创作中的种种用意,无不是出于对当下社会文化现实的真切关怀以及不无批判意味的反思。
无疑,如吴悦石先生这样的创作者,都身处某个必要的过渡或者转折期,因为还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文人画未来的命运,但可以确切感受到的,是困境甚至绝境。无论如何,吴悦石先生的坚守是不可忽视的。很简单,只有在保证文人画的存在之后,才能谈及其他。假设作为一种绘画方式的文人画业已荡然无存,那么无论理论上给予如何美好的预言,似乎都是无济于事的。这样看来,吴悦石先生的在无路之处的行走,其意义与价值也就不言而自明了。
中国书法网【盛世·大家】系列专题之
吴悦石
精品欣赏
/userhome/13335947